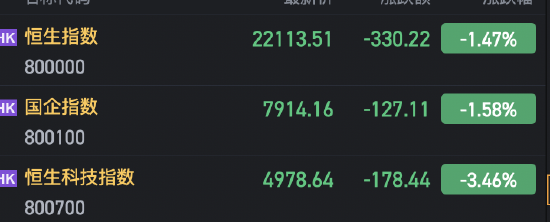世界文學新動向 |“那些感受不及時寫下就會消失”
1972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者中的亞洲身影
日前,1972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名單公佈,共100個提名名額,總101位被提名人。以提名數計,W. H. 奧登(W. H. Auden)負9名提名人,多數來自紐約;當年得主海因里希·伯爾(Heinrich Böll)負8名提名人,然而大部分被提名人只負一個提名人,其中不乏之後的諾獎得主。
 林語堂
林語堂亞洲受提名多達10位作家,占9個提名名額,其中有四位作家分享了兩個提名名額,四位作家中有一位另獨占一個提名名額。10位作家分別是黎巴嫩詩人與作家賽義德·阿克勒(Said Akl)、印度孟加拉語小說家塔拉桑卡爾·班代帕迪耶(Tarasankar Bandyopadhyay)、印度語言學家蘇尼蒂·庫馬·查特吉(Suniti Kumar Chatterjee)、印度靈修導師欽莫伊(Sri Chinmoy)、中國作家林語堂、韓國詩人兮山(Pak Tujin)、黎巴嫩詩人與評論家米哈依爾·努埃曼(Mikhāīl Nuaymah; Mikhāʾīl Naʿīmah)、黎巴嫩法語劇作家喬治·謝哈德(Georges Schéhadé)、以色列意第緒語作家亞伯拉罕·蘇茨科沃(Abraham Sutzkever)、越南詩人武黃遧(Vũ Hoàng Chương)。其中喬治·謝哈德負3個提名人,欽莫伊負2個提名人,其他均負1個提名人。此外,這是林語堂第四次被提名。
喬治·謝哈德生於1905年,與塞繆爾·貝克特、歐仁·尤內斯庫(Eugene Ionesco)、阿瑟·阿達莫夫(Arthur Adamov)大約同齡,他也是其時廣義的荒誕派潮流的參與者。謝哈德一生寫作了六部戲劇,讓-路易斯·巴勞特(Jean-Louis Barrault)指導了其中多部。謝哈德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黎巴嫩貝魯特,他曾在貝魯特高級藝術學院(École Supérieure des Lettres)任職,由於黎巴嫩內戰他於1978年定居巴黎,直到其1989年逝世。謝哈德深度參與了超現實主義及其後法國文壇的種種,他被普遍視為超現實主義者,1986年獲首屆法語國家大獎。
除以上提及的作家,與未來諾獎作家外,1972年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名單中值得關注的作家還有,比利時作家路易斯·保羅·布恩(Louis Paul Boon)、法語詩人艾梅·塞澤爾(Aimé Cesaire)、法國詩人勒內·夏爾(Rene Char)、加泰羅尼亞語作家薩爾瓦多·埃斯普里烏(Salvador Espriu)、法國小說家與散文家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芬蘭詩人帕沃·哈維科(Paavo Haavikko)、埃及劇作家陶菲格·哈基姆(Tawfiq al-Hakim)、匈牙利詩人裘拉·伊爾耶斯(Gyula Illyés)、符號學等學科現代奠基人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加拿大小說家休·麥克倫南(Hugh MacLennan)、瑞典兒童文學作家阿斯特麗德·林格倫(Astrid Lindgren)、美國猶太作家伯納德·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克羅地亞作家米羅斯拉夫·克雷紮(Miroslav Krleža)、法國哲學家加布里埃爾·馬塞爾(Gabriel Marcel)、波蘭作家斯瓦沃米爾·米洛傑克(Sławomir Mrożek)、波多黎各詩人埃瓦里斯托·里貝拉·切弗雷蒙(Evaristo Ribera Chevremont)、德國反法西斯作家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愛沙尼亞詩人瑪麗·安德(Marie Under)、羅馬尼亞裔小說家埃利·維賽爾(Elie Wiesel)、匈牙利詩人桑多·沃雷斯(Sándor Weöres)、美國戲劇家愛德華·阿爾比(Edward Albee)、美國戲劇家桑頓·懷爾德(Thornton Wilder)、美國小說家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意大利小說家裡卡多·巴切利(Riccardo Bacchelli)。
科馬克·麥卡錫雙新作
日前,科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在近日先後出版了一對小說,《乘客》(The Passenger)和《斯特拉·馬里斯》(Stella Maris)。兩部小說一主一次講述了鮑比·韋斯特與艾麗西亞·韋斯特備受折磨的人生,以及他們命定失敗的愛情。
 科馬克·麥卡錫
科馬克·麥卡錫《乘客》《斯特拉·馬里斯》都以恐怖的故事開頭。1980年,打撈潛水員鮑比被委派探尋密西西比淺水區一架沉落的飛機殘骸,黑匣子、飛行包、一具乘客屍體怎麼也找不見,隨後,鮑比被美國聯邦調查局追捕,似乎也被20世紀所有幽靈追捕。1972年秋,在威斯康星州的斯特拉·馬里斯天主教療養院,還在芝加哥大學數學系攻讀博士的20歲艾麗西亞被診斷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而在地球另一端,鮑比躺在醫院里,他被診斷為腦死亡。《乘客》文體相對如常,《斯特拉·馬里斯》則以艾麗西亞與精神科醫生的七次對話為主。
早在1980年代中期,麥卡錫就開始著手創作《乘客》。2005年,麥卡錫致信編輯說,某部關於新奧爾良打撈員的小說已接近尾聲。據稱,麥卡錫擅長多線工作,即同時經手多部著作或者多項工作。麥卡錫寫作時很克製,避免攜讀者去感受。這很像他的性格,不著急,掌控著自己的節奏。
這是麥肯錫罕見地以女性為主角。上一次麥卡錫將女性置於其故事中心還是《黑暗外域》(Outer Dark),它們有相似的亂倫情節。麥卡錫的女性角色比較刻板,懦弱、性感、受害。到了艾麗西亞·韋斯特,她則被授予了戈耳狄俄斯之結(Gordian Knot),共鳴症、精神分裂症、自閉症、厭食症、虛無主義,並愛上自己的兄弟。艾麗西亞疑似女同性戀,精湛於音樂,精研數學,而數學只是將其推向深淵。“言語智慧只能幫你走到某處,那裡有一堵牆,你不瞭解數字,就看不到這堵牆。牆另一邊的人們似乎讓你覺得很奇怪,但你永遠不會理解他們對你的寬容。他們將會很友好,或許不友好,這取決於他們本性。”艾麗西亞在小說中表達著對數學的癡迷。
兩部小說代表著麥肯錫對科學的再次貫注,小說男女主角都與量子物理有關,他們的父親參與了曼哈頓計劃。麥肯錫是研究複雜系統科學的聖菲研究所的受託人,為了表達對聖菲研究所的支持,麥卡錫將拍賣Olivetti Lettera 32手動打字機所得的20餘萬美元捐給了該機構。在聖菲研究所的辦公室,麥卡錫閱讀他的朋友麗莎·蘭德爾、勞倫斯·克勞斯等人的作品。2017年,麥卡錫與人合著了《凱庫勒問題》(The Kekulé Problem),論文聚焦於德國化學家奧古斯特·凱庫勒的夢,以及語言的問題。
1981年,麥卡錫由於索爾·貝婁等人的推薦獲得價值20餘萬美元麥克阿瑟獎金。麥卡錫借此前往西南地區,撰寫《血色子午線》,也就是他第一部在大眾閱讀和圖書市場的重要著作。借助麥克阿瑟獎金,麥卡錫結識了各領域的科學家,包括羅傑·佩恩和蓋爾-曼。他寧願將時間花在科學家身上,而不是文學家身上。
麥肯錫對知識,尤其是與身體相關的知識非常好奇。根據他早期一份珍貴的採訪,麥卡錫寧願談論響尾蛇、分子計算機、鄉村音樂、維特根斯坦,也不願談論自己和他的書。他沒教過書,沒寫過新聞,沒舉辦過讀書會和新書發佈會,極少接受採訪。麥肯錫文學中關於動物、風景、人的野性,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此。他成年後的很多時光都在營火圈外度過,與妻子家人在湖里洗澡。
小說中血淋淋的殺戮遠沒有其先前的作品多,但其殘酷並不下於它們。除了女主角經曆的深淵之外,男主角也是如此。鮑比在酒吧與無業遊民、酒鬼為伴,他的朋友都是費里尼式人物,騙子謝丹、脫衣舞女黛比。“邪惡沒有額外的終途,”鮑比對諾克斯維爾的酒吧夥伴說,“它根本不會接受失敗。”以海德格爾的“被拋狀態”形容麥卡錫筆下的人物有些軟弱,其實他們代表著黑暗與死亡,已無所謂被拋。人類無底的暴力與複仇,一直以來都佔據著麥肯錫文學的核心。
中國女作家“出海”潮:謝曉虹等
日前,香港小說家謝曉虹的《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英譯本由“陸上行舟”出版,“陸上行舟”是位於英國的一家獨立出版社,此前它“猜中”了多位諾獎作家,包括安妮·埃爾諾。該書是陸上行舟首部華語世界作品。
 《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英譯本
《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英譯本《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講述了教授Q不滿於苛刻的婚姻生活,與少女人偶愛麗詩偷情的故事。和皮格馬利翁的故事不同,愛麗詩在教堂、古典音樂、性愛的纏繞虛構中並沒有幻化成人,教授Q離開後,愛麗詩即變回人偶,最終成為浮屍。這與常規的敘事剛剛相反,主體性發生了一點萌生後又消亡了。謝曉虹將愛麗詩設置為一面鏡子,邊緣的、無法言說的,以此來促成讀者的反思。
謝曉虹在一次採訪中聲稱自己無意於記錄曆史事實,而熱衷於它們之後的感受。“曆史事實是有很多東西可以追認的——發生過什麼事、在哪裡。但是你當下那一刻的那些感受、和其他人的互動,你自己的經驗,其實那些都是某一種facts。我那時候有一個迫切性——不說出版——就是寫下,因為那些會消失的,你某一種的狀態。那件事讓你經驗到的精神、感受,是怎樣的,我需要在那個時候寫下。”謝曉虹表示。
謝曉虹是時下最重要的香港小說家之一。自2005年以來,謝曉虹先後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她最新的職務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她最早一本英譯本是《雪與影》,譯者是尼基·哈曼,《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譯者是納塔莎·布魯斯。謝曉虹先前一部作品是《無遮鬼》。同時,謝曉虹也是西西的研究者,西西創造了“我城”“浮城”等標誌詞彙。同時,謝曉虹也是《字花》雜誌發起人之一。
與《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推出的同時,英語世界對1970年後出生的中國小說家的關注主要以女作家為主。除謝曉虹外,張悅然、顏歌等人亦有至少一部譯作出版。顏歌更是早在多年前就定居愛爾蘭與英國,並開始英語寫作。
俄羅斯作家維·佩列文新作
日前,維·佩列文(Viktor Pelevin)出版新作《KGBT+》。佩列文是時下俄羅斯語文學中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也是最受讀者歡迎的小說家之一。佩列文的文學創作從蘇聯解體前幾年一直持續至今,可以說以平行時空的方式代言著俄羅斯那時以來的方方面面。
 維·佩列文
維·佩列文《KGBT+》由前一年出版的《超人類主義公司》(Transhumanism Inc.)發延而來,佐佐木先生就來自於此。在這個由佩列文虛構的世界,技術官僚稱許的神經網絡最終獲得了勝利,並統治了世界,富人們將自己的物理大腦保存到“罐子”就能獲得永生,而其他人只能在“打手”文化中浸淫。孤兒薩拉瓦特大腦里被植入了先進的技術物,他“進化”成了KGBT+,KGBT+和他的朋友們攜手進行了一場人類冒險,或者說文學與哲學冒險,很多佛教、神秘主義、賽博朋克片段像音樂一樣漂浮其中。
吸引佩列文的是當下的俄羅斯,而不是過去的蘇聯。他稱新一代俄羅斯人為“P一代”,P可以指“百事”,可以指佩列文,也可以指pizdets,這個詞是很粗俗的髒話。佩列文描寫了在俄羅斯社會普遍存在的內心流亡狀態,他們未必是持不同政見者,有著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那不過是偽裝罷了。
在蘇聯解體前幾天,佩列文完成了《阿曼·雷》(Oman Ra)。小說的背景源自其少年時期他在莫斯科軍事基地度過的漫長夏天。阿曼自小就癡迷飛行和深空,夢想成為像烏里·加加林那樣的宇航員和英雄。經過一番努力,阿曼被選入一個無人駕駛任務,他知道會迎來死亡,但也只好動身前往月球。但結尾顯示,阿曼從未真正過離開過地球,整個天空計劃都是假的。
超現實主義、科幻未來主義、黑色幽默,正是後來佩列文一貫的色彩。《智族人》(Homo Zapiens)中,悲慘的年輕詩人捲入虛構的政府;《S.N.U.F.F》中,新聞僱員生活在天之國彼讚季烏姆,他的機器人女友對其策劃著一場陰謀;《IPhuck 10》開篇就道,“人是一類特定的小惡魔,以別人的痛苦為食。”
有評論者曾指出,“如果從形式上判斷,佩列文是個後現代主義者,是個典型的後現代主義者:不僅從形式角度,而且根據內容——第一眼似乎如此……看得仔細些……,佩列文……事實上——在思想上、內容上——根本不是後現代主義者,而是地地道道的俄羅斯典型的思想型作家,類似托爾斯泰或車爾尼雪夫斯基那樣。”
佩列文生於1962年,生長於蘇聯時代末期。父親是沒有任何影響力的蘇聯軍人,母親是經濟學家。從莫斯科航空學院獲得工程學學位後,佩列文做過記者、廣告人、口譯員。佩列文始終保持獨立,並與文壇保持距離,但他也因此獲得了大批熱愛他的讀者。
兩屆斯特雷加獎得主桑德羅·韋羅內西
日前,改編自桑德羅·韋羅內西(Sandro Veronesi)《蜂鳥》(Il Colibrì)的同名電影《蜂鳥》上映。《蜂鳥》由弗蘭切斯卡·阿爾基布吉改編和執導。此前,《蜂鳥》獲得斯特雷加獎,這是桑德羅·韋羅內西第二次獲得該獎,此前從未有人兩度獲得該獎。
 桑德羅·韋羅內西
桑德羅·韋羅內西《蜂鳥》向讀者展示的是對生命、家庭、人心,以及“悲痛之獨裁”的沉思。事故從1980年到進展到2030年代,跨越四代人,在信件、詩歌、郵件、清單中不斷增殖。
眼科醫生馬可·卡雷拉娶了不忠的瑪麗娜,他們離婚了;而後馬可·卡雷拉愛上了露易莎,但愛而不得。馬可·卡雷拉的兄弟姐妹要麼疏遠了他,要麼自殺去世;而他的父母罹患癌症,患有情感障礙,且時常暴怒。馬可·卡雷拉背叛了自己的朋友,他的朋友曾救他一命。他的女兒在一場事故中去世,給他留下了一個孫女,他得照料。
馬可·卡雷拉的生命充滿悲傷、破碎,他將自己的問題歸咎於其生命中所有女人最終都被各種心理治療師控製了,他不厭其煩地將心理治療師區分於精神病醫生。還是露易莎給了他答案,“沒人能像你一樣堅持不懈,也沒人能像你一樣躲避變化……你穩紮穩打,一直堅持到最後,也致命地拒絕服從別人的規則或決定。”露易莎視其為蜂鳥,蜂鳥以12-80次/秒轉動翅膀時就可以在空中保持靜止,馬可·卡雷拉也花了他全部力氣使自己保持靜止。
桑德羅·韋羅內西生於1959年,在佛羅倫斯大學獲得建築學學位後才開始了寫作生涯。桑德羅·韋羅內西有很多國際讀者,比如蕾拉·斯利瑪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