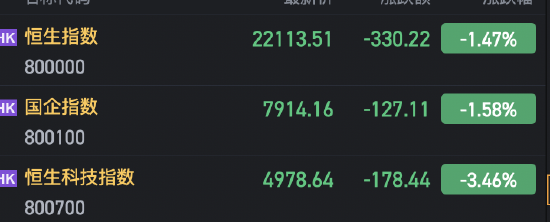陶熠評《萬里江湖憔悴身》|山川終要識詩人

《萬里江湖憔悴身:陳與義南奔避亂詩研究》,[美]王宇根著,周睿譯,王宇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380頁,98.00元
兩宋之際的戰爭喪亂和代際轉換為宋代士大夫文化心理與文學風貌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陳與義(1090-1139)便是這一轉型過程中的典型樣本。南奔避難的經曆助益了陳與義詩歌“簡潔”“雄渾”(劉克莊《後村詩話》前集卷二)風格的形成,而沿途的自然風景又隨詩人的情感激盪折射出了多元的色彩,可謂“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葛勝仲《陳去非詩集序》)。美國俄勒岡大學東亞系王宇根教授《萬里江湖憔悴身:陳與義南奔避亂詩研究》(Writing Poetry, Surviving War: The Works of Refugee Scholar-Official Chen Yuyi)一書關注的核心問題正是陳與義的山川行旅與詩歌技法間的互動關係。該書對中國詩學中“自然-作者-文本”三者相互干涉的細膩呈現,再次為英文與中文世界的讀者都奉上了頗具異質之美的他山之石。
與王宇根教授的前作《萬卷:黃庭堅和北宋晚期詩學中的閱讀與寫作》相較,本書同樣選取了一位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以文本細讀的研究手段,力圖開啟一條指向宋代詩學核心問題的方法之路。由於兩書研究對象的差異,本作不再選取閱讀史、物質文化為主要視野,而是參合陳與義多難飄零的一生,將其詩作“還原於詩意的原始語境”(中譯本18頁,下文頁碼均為中譯本頁碼),並針對陳與義“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張嵲《陳公資政墓誌銘》)的山水詩成就,將研究焦點轉向了中國文學傳統中的詩人與自然關係。
從詩騷中的興象譬喻,到六朝人的“應物斯感”(《文心雕龍·明詩》)與“江山之助”(《文心雕龍·物色》),詩人如何在自然中創造詩作始終是中國詩學的大問題。中唐以降,詩人從“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陸機《文賦》)的被動“感物”者,轉向了“古今百家景物萬象,皆不能役我而役於我”(楊萬里《感應雜著序》)的主動馭物者。這種觀念的差異也蘊藏在唐音與宋調的詩學差異之中,可以看作唐宋詩學轉型的重要表徵之一。在這一觀念轉變的驅使下,“詩眼巧增損”“江山拾得風光好”“萬象畢來,獻予詩材”等饒具宋詩風味的詩學表述紛至遝來。對這一問題,中國學者如周裕鍇、李貴,美國學者如宇文所安,日本學者如山本和義、淺見洋二等都有十分精彩且深刻的論述,並提出了“天與詩材”“轉物詩學”“文助江山”等一系列新穎的學術命題。這些已有研究討論的對象,多集中於宋詩風格的開拓者韓愈、柳宗元,宋詩的典範作家蘇軾、黃庭堅,以及南宋有意回向唐音的陸遊、楊萬里。而本書的一大貢獻,正在於將陳與義納入了自然與詩人關係流變的譜系之中。本書的導論便明言,作者在承認陳與義影響南宋中興詩人的前瞻性詩學取向之時,更有意將“陳與義視為標示著源自中古魏晉時期的山水詩的漫長演變的‘終點’”(第6頁)。這對重新理解陳與義的文學史定位無疑是頗具隻眼的啟示。
 清代三十六詩仙圖卷之陳與義
清代三十六詩仙圖卷之陳與義本書中文版雖然以“南奔避亂詩研究”為題,實則縱貫陳與義的一生,研究對象不僅限南奔途中的作品。第一至三章是本書的第一部分,首章《客居》討論了《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絕》等陳與義的早期名作,主要關注陳與義詩中敘事者視角以及藝術與真實關係等問題;第二、三章《年華》《貶謫》針對的則是陳與義政和八年至宣和七年(1118-1125)間的作品,指出這一時期的陳與義詩轉向私密、內省,是陳與義個人風格的形成期。
第四至七章為第二部分,討論陳與義南渡沿途的作品,也是本書的核心。第四章《前路漫漫》對應陳與義1126年至1127年南奔初期往返鄧州間的詩作,作者認為陳與義此間詩作中自然與詩人的關係發生了深刻轉變,即由冷漠對峙、互不共情豹變為近密互動、沉浸交流;第五章《山與水》涉及1128年陳與義自房州至均陽間的詩作,作者進一步比較了陳詩與杜詩,認為此時陳與義對杜詩的摹擬偏重詩情而非詩法,而漢水的旅途則助長了陳與義詩情自然抒發的趨勢;第六章《面對面》專論陳與義建炎二、三年間(1128-1129)的嶽州詩,以嶽陽樓與洞庭湖為例,揭示了黃庭堅對陳與義嶽州詩營求世界和諧有序的詩學影響,指出嶽陽樓、洞庭湖作為人文地理的重要符號,在陳與義的旅途漂泊中幫助他錨定了自我身份,更明言南奔旅途使陳與義“切膚入骨地遭遇自然世界”(261頁),使其詩中的自然更為親近、馴順;第七章《詩到此間成》對應陳與義1129-1130年間自嶽州至邵州的旅途,作者認為這是陳與義詩的大成期,並專題討論了陳與義的“論詩詩”,指出陳與義對南方景物的接受促成了詩人與自然親密無間的關係。
第八、九章《破繭成蝶》《煢煢獨立》為第三部分,速覽了陳與義紹興年間(1131-1138)的作品,涉及陳與義對嶺外景物的呈現,以及晚年心齋不住於物的自然觀。
從體例上看,本書可謂一部兼具現代評傳與傳統詩箋色彩的專著。以詩人行履討論詩風演變本是作家個案研究的經典體例,在本書之前,同樣以陳與義為研究對象的《陳與義詩研究》(杭勇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上編也採取了這一寫作思路。而本書與傳統方法之間的差異,一則在於鮮明的問題導向,二則在於對作品個案的細密闡發。就第一點而言,作者將自然與詩人的關係作為全書的主導問題,各章對具體詩作的分析也始終著眼於陳與義詩呈現自然的主觀視角,從而勾勒出了一條陳與義與自然關係轉變的顯豁線索,即從審美性的“遙觀”,轉向冷峻沮喪的“對峙”,終而變為親曆性、主觀性的近密無間。這是傳統的詩箋難以發現的曆時性結論。
就第二點而言,文本細讀幫助作者發現了潛藏在文本字裡行間的隱秘消息,如作者剖析《次舞陽》一詩收尾“嵯峨西北雲,想像折寸心”兩句時,就敏銳地發現了“西北”這一方位詞與陳與義行旅路線的齟齬。陳與義於靖康元年(1126)自陳留南奔至商水,此時則西折至舞陽。如此,無論是旅途的起點陳留,還是故國的都城開封,都應在陳與義的東北方,望“西北”之雲氣,或與當時的實境有悖。故而作者認為,陳與義詩中“西北”的方位是“象徵性”的虛指,不僅延續了“西北有高樓”“西北有浮雲”的漢魏詩傳統,更共享了杜甫在夔州遙望長安時,“歡娛兩冥漠,西北有孤雲”(《九日五首》其三)、“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鬥望京華”(《秋興八首》其二)的主觀視角。可見南奔途中的陳與義,不只是借用杜詩的語詞,更內化了杜甫的情感與視角,使自己成為另一個杜甫,甚至“連杜甫凝望的方向也全然照搬”(171頁),這顯然又是評傳很難觸碰到的文本細節。作者在註釋中承認此說受到宇文所安討論“孔雀東南飛”時的思路啟發,但就筆者目力所及,此處解讀本詩的具體結論尚未經人揭櫫,可謂本書作者的獨到發明。此類新見都得益於本書將曆時評傳與細膩詩箋相結合的體例選擇。
可玩味的是,不知是出於偶合還是出於作者的巧思,本書的體例恰恰和古人的江山行旅之間形成了一種同構性。在閱讀本書的同時,讀者很難不隨著陳與義的詩家之眼觀覽流難之間的山河破碎,真可謂“數千里山川在人目中”(朱弁《風月堂詩話》),而讀者的加入也補全了“世界-作者-文本-讀者”間的關係鏈條,當陳與義在親曆江山的同時,讀者也在體驗陳與義的親曆。這或許也能看出作者以語境還原為闡釋方法的用心良苦。
回到本書的主題,當作者將陳與義納入自然與詩人關係的轉變譜系,我們似乎能越發清晰地看待陳與義在文學史上的定位。一方面,陳與義的自然觀在行旅中超越了蘇黃等宋詩典範作者馭使自然、掌控自然的觀念,轉向對自然的平等相親。作者承認陳與義詩中確有反映詩人從外部自然擷取詩句的表述,如“海棠猶待老夫詩”(《用前韻再賦四首》其三)、“天公亦喜我,催詩出晚霞”(《九月八日登高作重九奇父賦三十韻與義拾餘意亦賦十二韻》)等,這一觀念的基礎正是宋詩馭使萬物的詩學主張,此寫法更下啟了陸遊、楊萬里等南宋詩人“拾得”詩句的寫作風習;但整體看來,陳與義的南奔旅程將他低迷的情緒投入了治癒性的山水之中,從而洗刷了他早期以自然為把玩客體的“傲慢”,自然觀的轉變使得他的詩歌呈現出不同於黃庭堅與江西宗派其他諸家的清新面貌。用作者的話來說,國家喪亂帶來的避難體驗,賦予了陳與義更強烈的情感能量和更直率的表達,“陳與義不再只是追求對眼中所見的物質山水景物的靈性超越,而是將它們納為他自我和身份建構的核心‘元件’”(第5頁)。這可以看作陳與義對唐詩傳統的某種回溯。
另一方面,在討論陳與義的詩學淵源時,作者又有意在杜甫與黃庭堅二者間尋求平衡。作者沒有天然接受陳與義全方位摹擬杜詩的判斷,而是在反覆的辨析中,試圖尋找陳與義詩呈現自然時的特異性。在作者看來,陳與義靖康後對杜甫的模仿不在詩法上,而是在情感體驗上,人生的巨變使他“在江西詩派影響下養成的內心的‘杜甫’遽然、猛烈地被激醒”了(第7頁)。與杜甫相比,陳與義儘管遭受了流寓之苦,但他一直努力為自然賦予平穩和諧的秩序,這與杜甫晚年詩中常見的不安、危險、失控的氛圍決然不同。作者認為,陳與義之所以沒有被異質的景物吞噬,正因為他繼承了黃庭堅等宋詩典範作家對個人內在修養的重視。同時,陳與義在措辭上更加強調現實指涉,他使用“三年多難”的實指,而非“百年多難”的浮詞,足以說明陳與義仍統屬在宋人追求“切當”的詩學主張之下。這可以看作陳與義對宋詩風味的延續。
王宇根教授的這部新著為重審陳與義的文學史地位付出了諸多方法論上的努力,唯有一處尚覺意猶未盡,即鮮少涉及陳與義與陶謝韋柳山水詩傳統間的聯繫。從本書關注自然與詩人關係的方法論上來看,這一傳統恐怕是不應被忽視的。同光體詩人陳衍評價簡齋即稱“宋人罕有學韋柳者,以簡齋為最”(《宋詩精華錄》卷三),近年也有學者指出胡穉的箋注過於強調陳與義詩的杜、黃淵源,遮蔽了簡齋詩備受讚譽的韋柳風韻(劉月飛《論陳與義的詩學淵源——以〈增廣箋注簡齋詩集〉為中心的考察》,《中國詩歌研究》第二十三輯)。如何從自然與詩人關係的視角重審陳與義在山水詩譜系中的位置,或可成為另一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此外尚應指出的是,本書中存在少量因文本擇取而產生的誤讀,如第四十七頁引用《雜書示陳國佐胡元茂四首》(其一)一詩,第三句作“願將千日饑”。實則國家圖書館藏元刊本《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作“顧將千日饑”,吳書蔭、金德厚點校《陳與義集》(中華書局2007年版)同元本,不誤。本書此處引文當沿襲自《陳與義集箋校》,但這一處異文似乎沒有文獻學上的其他佐證。詩句中的“顧”本就可表示輕微的轉折,言“顧將”,猶言“只將”“但將”。此句乃承一二句而來,首兩句曰“一官專為口,俯仰汗我顏”,是說自己本來不過是為了餬口而做官,王著將其理解為“用實用的語言、毫不含糊地表明其選擇的無奈”,尚可謂得間。三四句說“顧將千日饑,換此三歲閑”,乃是說自己初入仕途的收入就連餬口的現實需求也沒能滿足,遑論許身稷契的政治理想了,好在教授的職掌相對閑散,從而才感到又“饑”又“閑”。陳與義在開德府教授任上《次韻周教授秋懷》一詩有“一官不辦作生涯”之句,《次韻張矩迪功見示建除體》又云“滿懷秋月色,未覺饑腸虛”,可見陳與義政和三年至六年(1113-1116)的收入確不豐厚。如此,這四句說的就不是“以‘千日饑’換‘三歲閑’之‘願’”,而是牢騷與抱怨:他抱怨官俸的微薄,又慶幸事務的清閑。在陳與義看來,饑是次要的危機,不能得閑才是更高的危機。本詩五-八句應當只是單純的自比:我就像天空中的鴻雁,饑餓只是一時的,身纓羅網才是需要警惕的最大危機,所以不應該效仿杜甫,為五鬥米而以儒冠誤身,而是要儘早歸隱,以免晚年徒留懊悔。僅就本詩而言,陳與義並未表露出折衷調和“追求學術理想和滿足物質需求”的努力,反倒給出了早日歸隱的明確選擇。作者對異文的誤用,導致了對詩義理解的偏移,不能不說是白璧微瑕。
最後,作為一部2020年新作的譯本,本書的譯者周睿僅用兩年時間就為中文世界的讀者提供了如此流暢自然的譯文,不得不令人感佩。本書譯者不僅避免了通常譯本行文上的滯澀難懂,更為原著增添了豐富的譯註,糾正了原書中的一些筆誤,也補充了不少更便於讀者理解的註釋,如第八十四頁對“觀國”的補註,第九十頁對原著古今地名對應的糾正,都能看出譯者的格外用心。
總之,王宇根教授的這本《萬里江湖憔悴身:陳與義南奔避亂詩研究》可謂問題意識與文本箋疏兼備,學術之理與讀詩之趣並存的作品。相信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讀者既能通過作者的文本闡釋生發出學理性的聯想,也能在作者對時代遷轉的娓娓道來、對詩作語句的條分縷析中收穫愉悅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