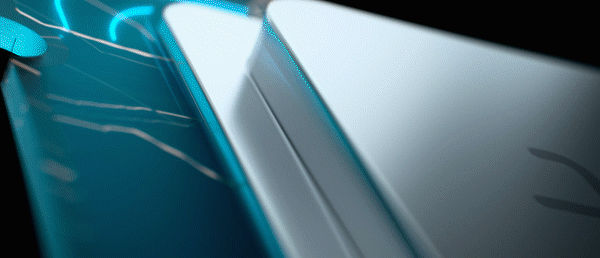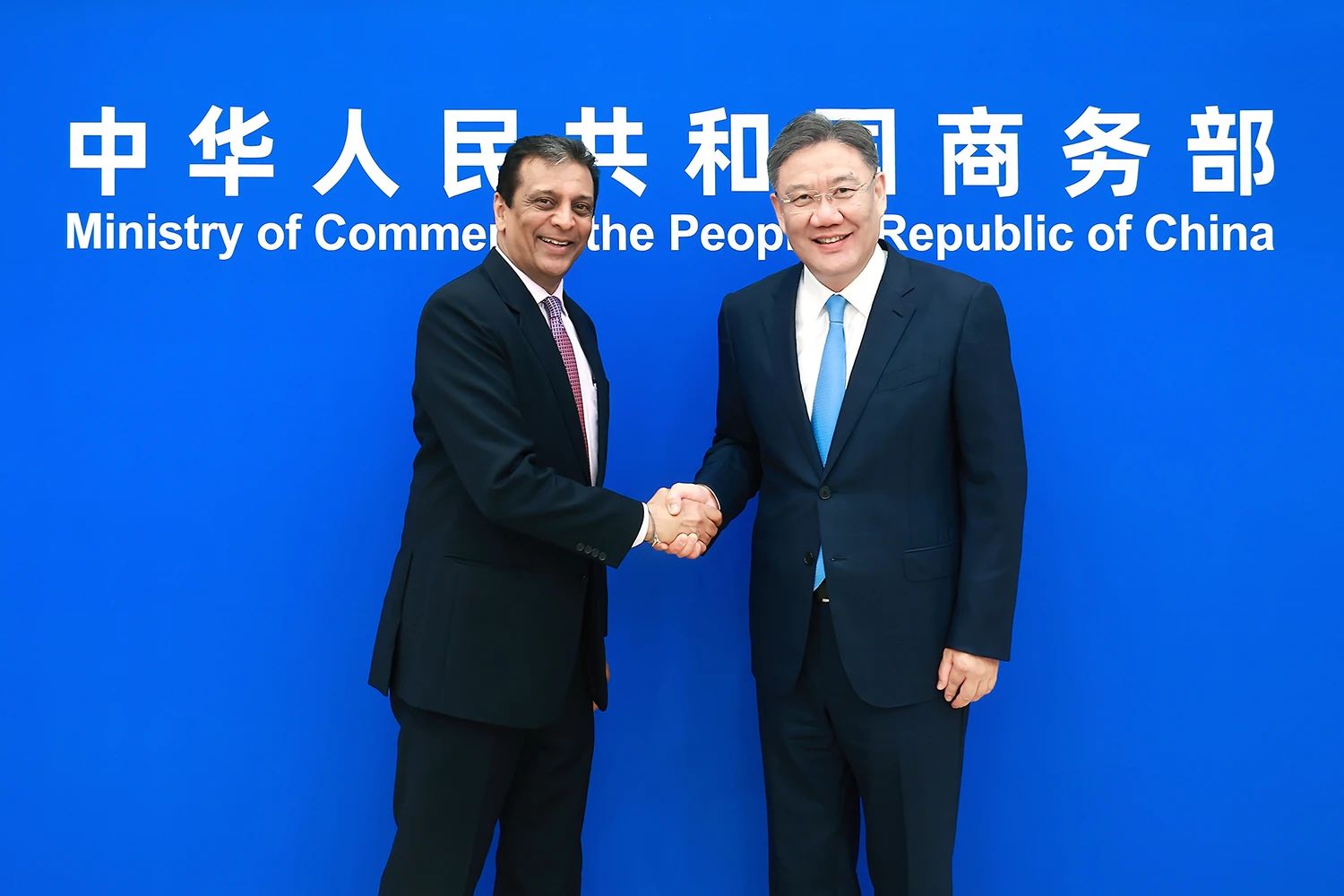《勇者》| 盲人張洪,站在世界之巔
珠峰是有聲音的。帳篷外高壓鍋突突冒氣的聲音,直升機起降嗡嗡的轟鳴聲,犛牛脖子上的銅鈴發出清脆的叮噹聲,哢嚓裂開、轟隆坍塌的冰崩聲。直到臨近8848米,風聲從耳後繞到頭頂,雪風呼嘯,雪坡平滑,周圍空曠,而且寂靜。
46歲的盲人張洪正是聽著這些聲音站上了世界之巔。2021年5月24日上午11點15分,天空呈淡藍色,大風吹散薄霧,陽光照耀著五彩經幡,它們覆蓋在略微傾斜的雪坡上,在凜冽的寒風中隨風飄揚,遠處的背景里,連綿的雪山冷峻而又莊嚴。
張洪穿著一身紅色登山服,戴著護目鏡,氧氣面罩,除了衣服上繡著的名字和五星紅旗,沒有人能看得出來他是誰。卡積亞巴嚮導抱著張洪說:「張洪,You Summit(你登頂了)。」張洪沒有力氣回應,他隱約聽到對講機里傳來人群歡呼的聲音。之前,他曾模擬過登頂之後要喊的口號,打算做的動作,在這一刻,全忘了。
張洪成為亞洲首位登頂珠峰的盲人,一路險象環生。距離登頂100米處,張洪的氧氣瓶調節閥凍住了,氧氣開始泄漏。嚮導強子和隨行攝影師,決定把自己的氧氣瓶留給張洪使用,他們放棄登頂,回到4號營地等候。張洪面對的是未知的前路和無法用中文交流的卡積亞巴嚮導,這是張洪最有感觸的情節,如實在紀錄電影《讓世界看見我》中呈現。
此後,和攝影師一同消失的,還有視覺能呈現的影像。登頂以及下山返回還有長達十多個小時的危險旅程,紀錄電影留給觀眾的是一片黑色想像,以及厚重的喘息聲。
張洪「聽」了五遍電影,周圍人的描述,幫他拚湊出視覺缺失的部分。
 2021年5月下旬,張洪攀登珠峰過程中。受訪者供圖
2021年5月下旬,張洪攀登珠峰過程中。受訪者供圖最後的死亡地帶
中文嚮導強子和攝影師離開後的故事,電影里沒有太多呈現。
在海拔8700米處,一般人缺乏輔助氧氣很難挺過十分鐘。為了保證張洪能夠安全登頂,包括強子本人和兩位攝影師在內的五人下撤,留下足夠的氧氣,讓三個狀態最好的卡積亞巴嚮導幫助張洪繼續衝頂。卡積亞巴,這是一個常年生活在喜馬拉雅山脈的民族,因給登山者當嚮導而聞名。每年,他們都會先行上山修好路繩,沿途背運氧氣瓶等補給,需要的時候救援登山者,人們則沿著路繩向上攀登。
張洪想過和強子一起下撤。強子對他說,「我們以後還有機會登頂,對你來說,你可能一生就這一次機會。」說完,強子推了張洪一把,讓他繼續前進。
剛剛分開的幾分鐘,張洪的腦子一片空白。他出於攀登的慣性,跟隨著前方一米多遠卡積亞巴的腳步,走了沒多遠他突然驚醒,感到了從未有過的「真正的恐懼」。
「我突然想到,不對呀,他們3個卡積亞巴一句中文都不會講,我也不會講英文,那怎麼弄?」在海拔8000多米處,風速將近60公里每小時,相當於七級風力。
黑暗中,登山者的頭燈連成一條彎彎曲曲的光帶。沒人拍照,沒人說話,一支靜默的隊伍。
 張洪一行人在攀登珠峰。受訪者供圖
張洪一行人在攀登珠峰。受訪者供圖那個時刻,張洪的感受是「快完了」。距離頂峰只有不到100米,放棄不甘心,繼續走凶多吉少,他靠著「我來幹啥來著?」「不怕死才能活得更好」這些心理暗示來緩解恐懼。
他和卡積亞巴用最簡單的單詞,「go、up、stop」來交流。在狂風呼嘯中,他們的嘴巴被氧氣面罩全部蓋住,即使這樣的單詞,也要靠吼才能勉強聽見。張洪問卡積亞巴還有多久登頂,對方回答,半小時。張洪感覺,走了很多個「半小時」,仍然沒有登頂。後來他才知道,全世界的卡積亞巴都是這麼回答登山者的。
在一個又一個「半小時」後,他們迎來了登頂珠峰的最後一關:希拉利台階。這是海拔8790米的一處高12米,近乎垂直的岩壁,這條身處「死亡區」的山脊是登頂的必經之路。因新西蘭登山家艾達馬田斯蒙·希拉利和尼泊爾卡積亞巴人丹增·諾蓋1953年首次登上珠峰取道於此而得名。
這條僅僅12米長的山脊,遠看像一片刀刃,幾乎是垂直的,寬度僅有30釐米左右,兩邊則是上千米的懸崖,通常只能允許一人通過,一些地方甚至只能放下半個腳掌。
從人類首次登頂珠峰至今,70年來,有近200位登山者將生命永遠留在了希拉利台階。張洪到達的12天前,一位瑞士登山者和一位美籍華人因為體能衰竭,在這裏失去生命。
到達希拉利台階的時候,張洪已經走不動了,冰爪在岩石表面容易打滑,站不穩。他只好蹲下,用一隻手觸摸安全的落腳點,然後支撐身體把腳抬出去,在這樣的反復中,花了近兩個小時順利爬上了12米長的希拉利台階。
張洪記得,後面的卡積亞巴曾大聲對他吼道,「No,No,Stop,Stop」,他趕緊收回了已經邁出去的右腳。
下山後從翻譯口中得知,卡積亞巴人衝他吼的地方,但凡有點偏差,張洪可能直接墜落2500米,自由落體2分鐘,「都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回憶人生」。
為什麼一定要登珠峰?
張洪在失明前從未見過珠峰的圖片。
在珠峰這個目標出現之前,他工作只是為了掙錢,單純為了活著,「但這不是我想要的」。不甘於生活平淡的張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有一個抽像的理想,想要做出點事,但在同樣長的時間內,他不知道那件「真正想要的」具體的事情是什麼。
身邊的人難以理解。好好做按摩,一輩子這樣平穩過去,這是99%的盲人能夠為生的手段,「好像我只能這樣過一輩子」。
從抽像到具體的路上,他折騰了很多年。
 2023年1月5日,北京,登山家、盲人張洪。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2023年1月5日,北京,登山家、盲人張洪。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張洪出生在重慶,父親和叔叔都是雙目失明的盲人,張洪是他們的盲杖。四五歲時發生的場景,張洪現在回想起來仍然清晰。年幼的他,用一根竹竿牽著父親和叔叔翻過大山,到十公里以外的鎮上乞討。
有一次腳下一滑,他們摔進了路邊的水田。一身泥水的張洪等來的是父親的責罵,嗬斥聲引來了圍觀的村民,在人們議論紛紛中,一顆怨恨的種子就此埋下,「為什麼我是盲人的兒子?」
後來,張洪考上了高中,但沒有條件上。他按照家人的建議去了成都,學按摩。在那裡,他結識了同樣學習護理的夏瓊,兩人談起了戀愛,那時的一切看起來都充滿希望。
但命運似乎沒有給他特別的垂青。21歲時,由於青光眼,張洪在短短三個月內完全失明。光明的未來突然墜入深淵,張洪變得暴躁易怒,他把自己關在房間,摔碎了幾個收音機,也想過結束生命。
夏瓊沒有離開,而是一次次阻止張洪自殺。當時他們在成都,沒有固定工作。夏瓊去批發小商品,擺起地攤。收攤後,她回家給張洪做飯,因為做飯口味問題,張洪發過脾氣;因為看不見,坐下的時候膝蓋碰觸到桌子,張洪怒吼過,把盛飯菜的碗碟摔碎。「看不見,這樣活著有什麼意思?」
夏瓊的委屈往心裡藏,她默默收拾完飯菜,躲到沒人的地方流淚。接受失明這一現實張洪用了近一年時間,日子在反復的暴躁內疚道歉中度過。在一片反對聲中,夏瓊依然選擇和張洪結婚。
婚後,他們開了按摩店,張洪手藝好,日日勤懇經營,生活漸漸安頓。他們買了房子,生了孩子,生活本可以一直這樣平靜下去。但張洪不願被盲人這一標籤限定人生邊界。
他把按摩店轉讓,帶著夏瓊輾轉昆明、上海,打工、繼續開按摩店、賣保險、做直銷,什麼都想去嘗試,要找到那一件「具體的事」。
因為孩子到了上學的年紀,張洪和夏瓊不得不離開上海,回到成都。2012年,張洪被西藏大學附屬阜康醫院聘為臨床理療科醫生。
 2012年,張洪被西藏大學附屬阜康醫院聘為臨床理療科醫生。受訪者供圖
2012年,張洪被西藏大學附屬阜康醫院聘為臨床理療科醫生。受訪者供圖不久後,他們舉家遷往拉薩,一個離雪山近的地方。
在拉薩,張洪結識了登山家洛則。洛則成功登頂了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在見面以前,張洪覺得登山家是偶像級的人物,他抱著崇拜的心情前往。在喝茶的過程中,洛則聊起登山的點滴,垂直的冰壁、危險的冰崩、遇難的隊友,這些遙遠而陌生的詞語,開始在張洪心裡留下印記。
他突然發問,「有沒有盲人登上珠穆朗瑪峰?」洛則回答,「有,一個叫Eric的美國人。」「我可以嘗試嗎?」就是這一句隨意的玩笑話,成為張洪人生中一個特殊的起點。
那是2016年,不喜歡運動的張洪,40歲的年紀開始出發。
40歲開始登山
張洪後來才知道,那位登頂珠峰的盲人Eric,從小就是運動健將,擅長摔跤、攀岩。相比之下,沒有運動經驗的他顯得「不知天高地厚」。
玩笑話說完的兩週以後,從徒步開始,洛則帶著張洪去拉薩周邊的山上練習。
張洪不知道有登山鞋、登山杖,他穿了一雙普通運動鞋,拿了一根盲杖,拽著洛則的胳膊,興致衝衝向上爬。因為海拔高,路上全是砂石,走路容易打滑,經常走幾步就會摔倒,張洪身上有了許多小擦傷。儘管如此,洛則肯定了他的反應力、平衡力、協調力。
就這樣,爬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張洪找到了登山的樂趣。雖然看不見,但是離開城市喧囂後的大自然,空曠、安靜,能聽見自己的呼吸,讓他感到放鬆、開闊。「你有足夠的時間和自己對話,也可以和大自然對話。」因為登山,他也逐漸打開自己封閉的生活圈,開始主動結識山友。
5800米的雪古拉峰是他第一次登頂的山峰。站在峰頂,山風呼嘯而過,吹得旗子招展,一種乾淨俐落的聲音。張洪更加確定了,登山,就是那個抽像的方向,那個一直在尋找的「具體的事」。
他不只是為自己,也想為夏瓊和兒子做點什麼。從夏瓊決定和張洪結婚那時起,她似乎和原生家庭漸行漸遠,失去了娘家的尊重和支持。張洪也比任何人都瞭解作為盲人的兒子會面臨什麼,他不願意兒子一直經受外界的輕視。
張洪想要證明夏瓊的選擇沒有錯,想給兒子樹立榜樣。但這種贏得尊重的方式一定是登珠峰嗎?
夏瓊沒有這樣的遠大理想,她更願意平靜安穩地相守。張洪為她去做的,是她想要的嗎?以可能付出生命的方式去向別人證明自己?有這個必要嗎?也許這樣的追問在兩個人的內心深處不一定有同樣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夏瓊再一次在擔憂、不安中選擇了支持。
2016年7月,張洪在一次登頂珠峰的分享會中主動結識了澤龍。登山家澤龍曾經在下山途中出現雪盲,在什麼也看不見的情況下,安全下山,這給張洪莫大鼓舞,他覺得,看不見,也是可以登珠峰的。
 2021年5月,張洪在嚮導的輔助下,借助路繩的牽引向上攀登。受訪者供圖
2021年5月,張洪在嚮導的輔助下,借助路繩的牽引向上攀登。受訪者供圖此後幾年,張洪陸續登頂了幾座海拔7000米的雪山。
但並不是一帆風順。2017年12月,澤龍帶領張洪攀登卓木拉日康的峰頂。下山途中,時間很緊,澤龍讓張洪坐在滑雪板上,他在後面用繩子拽住來控制方向和速度。突然,張洪感到腳碰到了一塊硬硬的邊緣,但他不知道是什麼。
澤龍指導他右腳踩住雪地,慢慢向右轉身,再上前幾步把他扶起來。等張洪站穩以後才知道,剛才,他已經滑到一個冰裂縫的邊上,左腳已經懸空,如果再向前半步,後果不堪設想。
這是張洪與死神的一次親密接觸。
有些微妙的情緒也在這時開始滋生出來。張洪開始反問自己,「我為什麼要來這裏呢?別人登山可以欣賞無與倫比的美景,也可以拍出很棒很酷的照片,那我的收穫是什麼呢?」
問歸問,問完之後,這依然是他那時為止能找到的目標。
「你一個瞎子,你認為真有人支持你嗎?」
普通人從尼泊爾攀登珠峰大概需要5萬美元。
一個盲人呢?
交通、帳篷、物資、餐飲、保險,比普通人需要更多的卡積亞巴嚮導,因為這些後勤保障,盲人攀登需要的費用常常是普通人的三四倍,大約是15萬-20萬美元。張洪面臨的首個困境是,錢從哪裡來?
不花這麼多錢的時候,張洪可以憑藉自身的毅力去登山。但珠峰不同,靠自己一個人走不通了。張洪曾放下面子,跟親戚朋友借,「我要去登珠峰」,這在農村百姓看來是「瘋子」行為,既沒有冒險的必要,更不值得花錢,他收穫的往往是陰陽怪氣的嘲諷。「你一個瞎子,你認為真有人支持你嗎?無非是同情你、可憐你,不願意傷害你而已,你還是老老實實做你的按摩養活自己吧。」
但夏瓊支持,她和親戚說,「他都已經看不見了,我們沒有理由阻止他追求夢想。」她陪著張洪訓練體能,去健身房,去爬樓梯。張洪常常四點鍾、五點鍾爬起來,在海拔3600多米的拉薩,穿著高山靴負重30多公斤,爬12層的樓梯,來回20多趟。
 2020年,張洪在健身房進行力量訓練,為攀登珠峰做準備。受訪者供圖
2020年,張洪在健身房進行力量訓練,為攀登珠峰做準備。受訪者供圖張洪的嚮導也換了。嚮導名叫強子,擁有十多年的高山攀登經驗,從這個時候起,攀登珠峰的團隊算正式組建了——只有他們兩個人。一個是登山經驗較少的新手,一個是沒有與盲人相處經驗的教練。
他一邊幫張洪做體能訓練,一邊總是發出最直接的靈魂拷問。「你都不會攀冰,要怎樣通過飄忽不定的隨時可能崩塌的昆布冰川,怎樣爬上垂直的冰壁,還有縱橫交錯的冰裂縫。這些對常人來說都很睏難,你怎麼過得去?你怎樣面對長達數百米的洛子壁,又怎樣躲避掉下來的石頭和冰塊?還有每一年都有人遇難的希拉利台階,你怎麼上?」
 張洪正在借助橫梯通過冰裂縫,下面往往是幾十米甚至幾百米的深淵。圖片來源:紀錄電影《讓世界看見我》
張洪正在借助橫梯通過冰裂縫,下面往往是幾十米甚至幾百米的深淵。圖片來源:紀錄電影《讓世界看見我》在出發之前,包括張洪在內,沒有人確定能籌到錢,更沒有人能確定他的身體做好了準備。
一邊體能訓練不能放鬆,一邊籌錢,張洪的心理壓力很大。強子常常說張洪繃得太緊,好像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那座山上。張洪也緊張,紀錄片團隊已經介入了,正在跟拍,「如果最後去不成,對別人來說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在出發前一年,他還沒有籌到一分錢。為了借款,他會為一些商店開業的活動站台,他向朋友開口,頻頻喝白酒碰杯,最後吐得不省人事,朋友卻在電話的頻繁催促中離開了,當然好在最後對方為他提供了幫助。除了自己籌集的部分,基金會幫忙,企業贊助,他所在的西藏阜康醫院也幫忙,五千美元五千美元的累加,在低頭、放下自尊、拋開別人的重重疑慮之後,錢終於湊夠了。
錢夠了身體可以嗎?一路上關於成功和失敗的可能性,頻繁在他心裡膠著,如果攀登不成功,餘生該怎麼生活?在爬樓梯,在四女生山集訓,這種成敗的想法每天都在心裡出現,並且隨著時間的臨近沒有任何緩解。
他做好了心理準備,如果努力過了仍然失敗,也許就接受,「我只能過這樣的生活。」
在出發尼泊爾之前,他帶妻子夏瓊去了海邊。這是一場告別之旅,之前相伴數十年,去看大海的夢想夏瓊常在他耳邊念叨,但是過去張洪對遊玩沒有心思,只想埋頭做那件「特別的事」。
直到要出發去攀登珠峰,不知道去了能不能回來,也許是生離,也許是死別,他心想,如果回不來,至少帶妻子實現一個簡單的願望。
夏瓊在海邊,說了一句讓他大為驚訝的話,「你的夢想是嚮往高山,我的夢想是嚮往大海,事實證明,高山和大海是可以在一起的。」
兩天后,3月30日,張洪坐上了去往尼泊爾的飛機,正式開始他的珠峰挑戰。
「生命是被動的」
海拔5943米的珠峰南坡大本營,彩色帳篷綿延一兩公里,四周冰川遍佈。能看到日照金山,也能聽到「轟隆隆」的雪崩聲。
大本營像一個地球村,彙聚了上千人,有登山者、嚮導、醫生、廚師等。這裏設施相對完善,餐室、廁所、充電板一應俱全,還能吃上麻辣火鍋。每天,直升機在山頭來回穿梭,運送物資,幫助救援。
張洪在這裏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做完了行前準備、和卡積亞巴嚮導磨合、進行高海拔適應訓練、登山裝備的適應性訓練等。
他們先是在崩塌的地面上走,耳邊不時傳來冰崩和雪崩的聲音,張洪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本能反應是快跑。因為看不見,總覺得崩塌的聲音就在附近。強子會提醒他冰崩離得很遠,可以放輕鬆。強子還說,因為看不見,張洪的刺激點應該比普通人更高。在訓練初期,強子似乎還不能對「看不見」感同身受,不能理解聲音帶來的恐懼。
 到達珠峰大本營後,強子帶領張洪進行攀冰訓練。受訪者供圖
到達珠峰大本營後,強子帶領張洪進行攀冰訓練。受訪者供圖當張洪在隊伍中停下來調整呼吸,他會毫不客氣地催促,「後面所有人都在等著你」。如果速度太慢,大大拉長到下一個營地的時間,將對體能造成極大消耗,快速通過才能降低風險。「珠峰不會因為你一個盲人給你大開綠燈。」這樣直接而坦誠的交鋒在他們登山過程中並不少見。
當張洪因為攀冰集訓受挫,想要減少集訓保存體能,降低風險的時候,兩人曾經發生過爭吵,張洪幾乎是脫口而出,「你叫個直升機,我今天就回去。」「你之前沒有攀過冰嗎?你翻臉不能比翻書還快!」
直到強子蒙著眼睛在碎石地裡走了一圈。他每邁一步都小心翼翼,伴隨著遲疑和慌張,最後腳步停下的地方,也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摘掉眼罩後,他和張洪的微小芥蒂似乎也破解了,他多了幾分理解。「確實不應該催他,可能我以前認為這裡面缺少了信任,其實,在他的世界裡面,可能這個信任已經給到了最多,或者給到了極限。」
準備一個多月後,剩下的就是靜待登頂的窗口期了。每年,攀登珠峰的窗口期集中在五月下旬那十多天,需要天氣足夠晴朗、風力足夠溫和。因為連日大雪,氣候惡劣,張洪推遲了兩次出發日期,錯過窗口期,前期的所有努力將付諸東流,內心的焦慮和無助蔓延到團隊每個人身上。
等待期間沒有任何事可做,張洪的膽囊炎還復發了。他側身躺在帳篷的床上,隆起的橙色蓋被微微抖動,隱隱聽得到幾聲輕微的嗚咽,極寒、缺氧、病痛、不可預估的窗口期,種種困苦細密交織在一起,他蜷縮在被子裡哭,吃不下強子端來的任何食物。事後張洪感慨,「生命是被動的,有再多的錢再強的團隊都左右不了天氣。」
2021年5月19日,也就是當年最後一個攀登珠峰的窗口期,夜裡,張洪、強子、攝影師以及其他幾個卡積亞巴嚮導出發了。之所以選擇夜裡,是因為夜裡氣溫低,冰川穩定。
沿途縱橫交錯不計其數的冰裂縫是危險的存在。強子指揮,張洪用腳來回反復試探,再用登山杖確定位置和穩定重心,有時張洪需要幾分鐘甚至十幾分鐘,才能跨過別人一步就能過去的冰裂縫。
更長一些的裂縫,則需要借助橫梯。
梯子的寬度剛好能放下兩隻併攏的腳掌,兩根橫樑之間的距離,剛好能容納冰爪腳尖和腳後跟卡進齒縫間,跨一步,插進縫裡面,提起腳,再跨一步。橫梯一次只能通行一人,兩頭用冰錐和繩子固定在岩冰上,走起來搖搖晃晃,兩邊只有繩子作為輔助保護。
這就要求張洪每跨出一步都必須全神貫注、準確無誤,落腳稍微有偏差或者是跨步過大過小,哪怕只是一釐米,就可能掉落冰縫。「那個時候你靠不了任何人。」
冰縫下面往往是幾十米甚至幾百米的裂縫,看得見的人雖然利於卡準橫梯的齒縫,但夜晚低頭行進的時候,看著腳下白色冰壁中透出一股冰藍的幽暗深淵更令人害怕。
張洪隊伍里的卡積亞巴就曾發生過意外,掉進了10多米深的冰縫裡,團隊合力用繩子把他拉上來,幸好沒有大礙。他們也曾在路上遇到登山者屍體,強子會瞞住張洪,讓他誤以為只是在和迎面相遇的人讓路。
四天之後,他們終於來到了海拔8000米的四號營地,等待最後衝頂的時刻。
登頂之後
在珠峰攀登史上,超過90%的死亡事故是從海拔8000米開始的。
位於尼泊爾的珠峰南坡4號營地,海拔8000米,被攀登者們稱為死亡地帶,真正的生命禁區。
2021年5月23日晚,衝頂出發前,強子再一次彎腰幫張洪緊了緊卡在高山靴中的冰爪。直到攀登十個小時後,氧氣瓶泄漏,剩下的旅程強子退出。
第二天上午11點,張洪登頂。他記得,出發前,營地指揮沃吉達·艾迪對他說過,「頂峰不是最終的目標,登頂只是一半路程,你的最終目標是回到大本營。很多人只想著登頂,他們一直使勁往上,用盡了所有力氣,登頂後他們欣喜若狂,也耗盡了最後的力氣,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事故都是在登頂之後發生。」
張洪牢記這番話,他簡單拍完幾張照片以後,就催促嚮導趕快下撤。
下撤的路上,風雪猛烈,張洪不記得摔了多少次,有一次摔倒之後,他筋疲力盡,甚至陷入了短暫失溫,「眼睛剛剛閉上就一下子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舒服。」不冷了,外面的狂風也聽不到了,全身細胞放鬆了,身體好像飄起來。
沒有沉浸幾秒,張洪被卡積亞巴喚醒,睜開眼依然是暴風雪,身體依然發冷,張洪意識到,一旦閉眼,可能不會再醒過來。在卡積亞巴的幫忙下,張洪強忍著極致的疲憊起身,繼續前行。
5月27日張洪終於回到了出發的地方——南坡大本營。那一天,他吃了很多東西,餅乾、奶茶,直到脫去冰爪,雙腳徹底回歸大地。
 2021年5月24日張洪登頂珠穆朗瑪峰,卡積亞巴嚮導和張洪(右)合照。受訪者供圖
2021年5月24日張洪登頂珠穆朗瑪峰,卡積亞巴嚮導和張洪(右)合照。受訪者供圖在拉薩的夏瓊也在第一時間接到登頂成功的電話。回想告別前,她曾和張洪拉鉤蓋章,她在車下,張洪坐在車上。隔著車門,她聲音哽咽,流著淚對張洪說,「不管上不上得去,都要平安回來,你自己的老媽你自己回來養,你自己的兒子你自己回來教!」
張洪戴著墨鏡,臉上看不出表情,沉默。關上車窗,行駛百米後,他在車上默默流淚。
他的承諾,做到了。
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