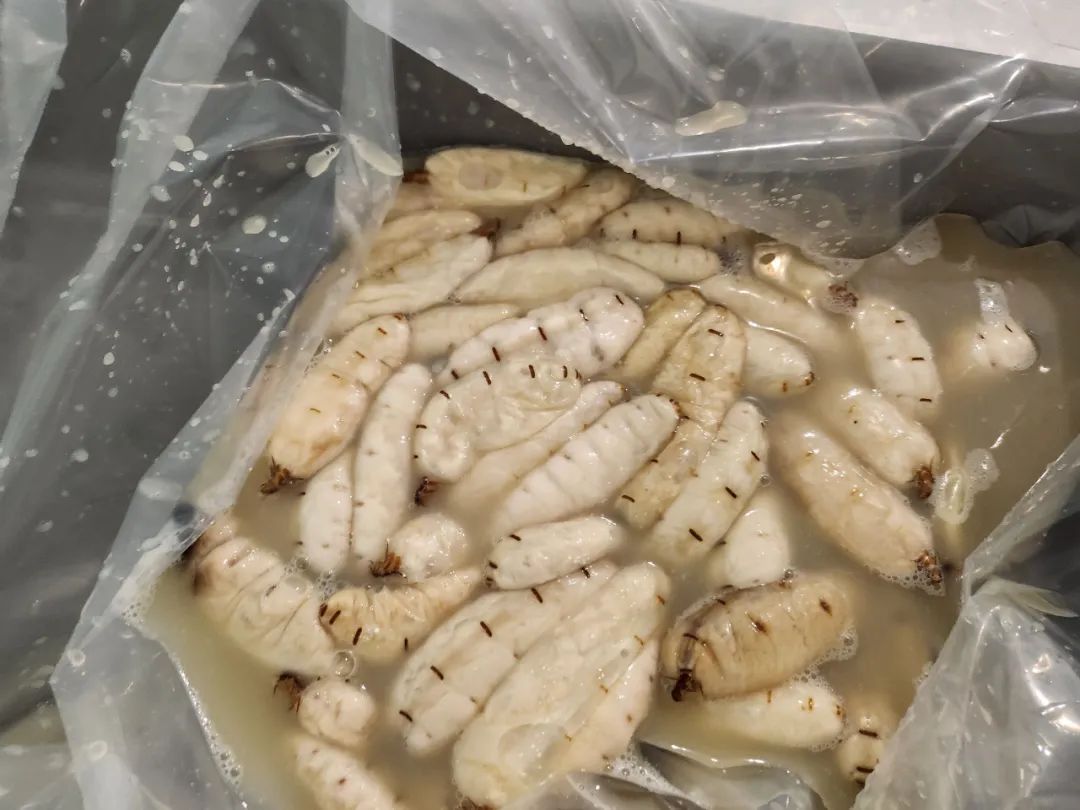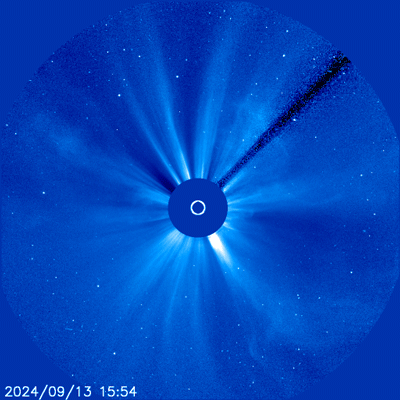失能老人,尋找最佳落腳點
四五年間,劉芳老伴兒手裡握著的東西經歷了快速變換——先是枴杖,隨後是助行車,最後變成了輪椅的操縱杆。即使如此,78歲的劉芳也依舊相信,她可以和老伴兒相互扶持著走完最後的人生。
直到83歲的老伴兒在一次洗澡後跌倒在地,她看著對方雙手顫抖,神色無助,卻不知道怎麼才能把他扶起來。劉芳意識到,她和老伴兒的養老,已經只能託付給別人。
如今,在豐台的一家養老驛站,電視里播放著老電影,劉芳扶著老伴兒從輪椅上緩慢站起,又在桌旁坐下,她說:「現在,這就是家了。」
據民政部門統計,北京市戶籍人口中有26.6萬重度失能失智的老年人。醫院往往是他們失能生活的起點,卻無法長期停留。90%的失能老人會選擇居家養老,但這意味著家屬要會面臨巨大的照看成本。最後,一些老人和劉芳一樣,選擇進入養老機構。
與能自理的老人不同,失能老人往往需要更專業的照料、更長期的醫療服務。醫院、家庭、養老機構,各有優勢和局限,失能老人該如何選擇自己的落腳點?
醫院長期住院難,多數老人選擇居家養老
「人失能了,就像在走一個這樣的坡。」養老驛站里,劉芳用手在桌子上畫了條長長的、向下的斜線,她說這是一個緩慢又坎坷的過程。在她的記憶里,這條「斜線」的起點是醫院,老伴兒得了淋巴癌,住院兩個月,十幾次化療,身體一天天變差。
醫院往往是老人失能後的第一站。他們在這裏接受治療,也在這裏和家屬一起適應失能後的生活,尋找養老去處。
對於失能老人和家屬來說,醫院是一個理想的「養老」場所。一方面,失能老人大多都有醫療和長期照護需求,醫院能最大限度滿足。另一方面,住院可以使用醫保報銷,能節省大部分「養老」費用。
一家民營醫院的負責人告訴新京報記者,失能老人在他們醫院產生的床位費、醫師服務費等費用,均可使用醫保報銷,而且老人醫藥費的報銷比例多為90%,「自費部分很少。」
但想長期留在醫院是很難的。唐蕾的父親因為腦溢血長期臥床,她輾轉了多家醫院,發現大醫院往往只讓住院兩三個月。最終,唐蕾還是帶著父親回了家。
多位醫生也告訴新京報記者,床位緊張、「壓床率」考核、報銷上限等因素,都讓大醫院不願收治失能老人。
在北京懷柔嘉惠社會工作事務所工作、為失能老人提供心理指導服務的白蘭發現,她接觸的大部分失能老人在離開醫院後,都更傾向居家養老。「金窩銀窩都不如自己的老窩,家裡會讓老人有歸屬感,比較自由,也能夠隨時看到孩子們。」
「在老人的觀念里,沒兒沒女、兒女不管的老人才會住養老院。」老伴兒出院後,劉芳幾乎沒有猶豫,就選擇了帶老伴兒回家。她擔心老伴兒住養老院有心理壓力,擔心養老院的護工虐待老人,也擔心老伴兒無法適應養老院統一的作息時間,「我們覺得在家才有安全感。」
一項數據印證了劉芳的想法。中消協公佈的《2022年養老消費調查項目研究報告》顯示,希望在熟悉的環境中養老,是老人選擇居家養老的最主要考慮因素。
很長一段時間里,劉芳覺得居家養老的生活自由舒適,她每天出去買菜,給老伴兒做飯,天氣好的時候就推著老伴兒出去走走。到了週末,三個女兒輪流來家裡看望二老,陪老人聊天,「他(老伴兒)每天覺得自己的生活棒棒的,不會感覺到自己被拋棄。」
但隨著老伴兒失能程度越來越高,生活的難題開始慢慢浮現。老伴兒起身,需要劉芳弓著身子緩慢攙扶,老伴兒洗澡,劉芳得讓老伴兒坐到凳子上再一點點擦拭。對一位78歲的老人來說,這些行動需要大量的體力和時間。
買菜、做飯、收拾屋子,這些原本兩個人承擔的家務都要劉芳自己來做,她還得照顧老伴兒的飲食起居,持續了一段時間後,她逐漸力不從心,有時不願意做飯,就點外賣,生活開始失去原本的規律。
老伴兒摔倒的那一晚,劉芳看著他坐在地上發抖,拿起電話,卻不知道該打給誰。她想聯繫女兒,發現她們住得遠,「等過來估計已經來不及了。」打給居委會和物業,可晚上十點半電話無人接聽。最終,劉芳報了警,在警察的幫助下才聯繫上物業,對方派人過來把老伴兒扶了起來。「如果再晚一會兒,可能就再也起不來了。」
像劉芳這樣的家庭並不少見,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2020年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95%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由家庭成員照料,且子女不再是主要的照料者,一半以上失能老人由其配偶獨立照料。因為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差,照料專業度低,這樣的照料方式往往面臨種種困難,甚至還會對照料者產生負面影響。
複旦大學艾靜怡、封進和上海財經大學餘央央三位學者研究發現,照料配偶增加了照料者發生抑鬱、身體疼痛以及其他健康問題的可能性,照料時間長短對健康的負向影響有明顯作用,照料時間越長,負向作用越大。
那次老伴兒摔倒後,折騰一圈總算脫險。但劉芳再也沒有了安全感,她意識到,如今自己和老伴兒就像瓷器一樣格外脆弱,僅有兩人獨居,已經受不起任何一絲意外。
 居家養老的老人借助扶手行動。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居家養老的老人借助扶手行動。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子女照護壓力大,居家養老常「失衡」
除了由配偶在家照料外,大部分失能老人都選擇由子女或其他家庭「勞動力」照料。
北京市老齡辦、北京市老齡協會發佈《2022年北京市老齡事業發展概況》顯示,北京市老年撫養係數持續上升,為近十年增幅最大。按15到59歲勞動年齡戶籍人口撫養60歲及以上戶籍人口計算,老年撫養係數為51.1%,比上年增長3.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平均北京每2名戶籍勞動力就要撫養1名老年人。
於靜就曾是其中的一個「戶籍勞動力」。95歲的母親失能後,她回到家裡「全職」照顧母親。她對母親的養老有著細緻的規劃,想讓母親的老年生活「不光是活著,還要有質量。」
在她看來,市場上的養老機構雖然也有很精細的服務,但很難像她一樣瞭解母親——低油低糖的飲食、唱歌的愛好、難以捉摸的脾氣,「這些在養老院很容易被忽視。」
每天上午九點,於靜就推著母親到小區廣場遛彎兒。母親會坐在輪椅上,笑眯眯地聽其他老人聊天。有時來了興致,她揮手打著拍子,唱一首《東方紅》。
「能看得出老人是真的很高興。」每次母親唱歌的時候,於靜都感到欣慰。在她看來,由家屬「一對一」「多對一」地居家照顧老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老人的生活質量。
但長時間的陪伴和精細照顧,也意味著家屬要承擔更大的情緒壓力、照護壓力。記者在採訪中發現,照料一個失能老人往往會調動起幾個家庭,甚至幾代人的時間、精力以及金錢。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在母親失能後,曹瑤對這句養老圈子裡流傳的話深有體會。母親因糖尿病併發症偏癱後,她帶著母親住進了外婆家,三代人共處一室。
母親想抽菸,有脾氣的外婆不讓,兩人經常吵架,她得站出來勸;與母親有矛盾的舅舅把曹瑤罵哭,母親一句沒幫,讓曹瑤難過了很久。
在曹瑤看來,母親性格原本就不好,失能後,她和母親聊天,總能感覺到母親有很強的「被拋棄感」,情緒也漸漸變得極端。在三代人共處一室的環境下,錢、居住空間和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能變成吵架的導火索,居家養老的兩週里,她常常覺得自己像塊「夾心餅乾」。
 居家養老的失能老人。新京報記者 王貴彬 攝
居家養老的失能老人。新京報記者 王貴彬 攝「比起照顧老人的體力勞累,更讓家屬難受的是心力交瘁。」於靜說。母親失能後忽然變得孩子氣,夏天捂著幾層被子吹空調,晚上一個人跑去廚房偷白糖,「我的神經一直得緊繃著,生怕她自己亂動摔著。」做飯的時候,於靜也要每隔半分鐘跟母親說句話,「這樣才能確認她沒有自己亂動,不會有危險。」
像於靜一樣「低齡老人照顧高齡老人」的狀況,成了失能老人家庭的常態。這一代人往往「上有老,下有小」,既承擔著退休前的工作,又不得不面對父輩、孫輩的照看壓力。
退休前,她要獨自一人撫養失能的母親、半失能的婆婆、還沒上學的孫子和癱瘓在床的丈夫,她把這些形容為 「四座大山」,「那是段昏天黑地的日子。」壓力最大時,她一度想帶著全家尋死。
快到70歲的房女士也面臨著這樣的養老困局,母親失能後,她發現就連簡單的幫老人翻身、扶老人上廁所,自己都沒有力氣做到。母親在弟弟家住了幾個月,弟弟家裡突然有事,老人又無處可去。直到後來去了養老機構,她才發現老人的尾椎附近的皮膚已經長了褥瘡,這讓房女士有些愧疚。
「家屬很難給老人專業的照護。」房女士意識到,失能老人的照護需求往往是全方位的,甚至是「24小時」的,而家屬很難有精力一直盯著老人,也不具備護理的專業知識。
入住養老機構:失能失智老年人平均佔比超85%
去養老機構,把衰老、脆弱的身體交給相對專業的人照料,這是劉芳和房女士為家人做的最後選擇,也是不少失能老人的最終去處。
根據北京市民政局公佈的數據,目前北京選擇機構養老的老年人中,失能失智老年人平均佔比85%以上,是養老服務的剛需群體。一家老年公寓院長也感受到,近幾年,護理型非自理的老人入住比例在逐年增加。
對於失能老人和他們的家庭來說,養老機構無疑可以提供更加專業的照護。
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房女士的母親都在床上度過,日常起居全靠人看護。到養老院前,她尾椎附近皮膚髮紅破皮,快要生褥瘡,經過護理員擦洗、上藥後,很快就恢復了健康。
此外,老人的一日三餐都是葷素搭配,保證營養;有兩班人手24小時輪流照看,以防老人有不時之需;護理員還會給老人定期洗澡、定時體檢,隨時留意他們身體的變化……這些都讓房女士感歎:「我們不專業,自己在家也留意不到,也辦不到。」
從事養老照護8年的周麗解釋,失能老人皮膚脆弱敏感,長期平躺容易生褥瘡,必須時常為他們翻身擦洗;一旦生了褥瘡,就要及時擦藥治療;腳踝處長期與床單摩擦,血液循環不暢,最好要騰空;如果老人三四天沒有排泄,就要及時處理,以免發生腸梗阻;重度失能老人還要通過鼻飼進食,他們的營養更要保障……而這些服務技巧要經過長期培訓、鍛鍊才能被熟練掌握,「家屬沒接受過培訓,有時很難做到,甚至容易受傷。」
而在78歲的唐琴看來,養老機構可以解決她最迫切的養老需求。
她在一家養老院住了快兩年,入院前,她先後做了三次髖關節和膝關節置換手術,只能靠助行器和輪椅出行,老伴兒也因為腦出血後遺症,喪失了語言能力和部分行走能力。子女還有工作,無法24小時照護他們。而在這裏,每個月花費6000元就包吃包住,也有護理人員照顧。
多位失能老人在受訪時提到,來到養老機構意味著「不給子女添負擔」——孩子們只需要定期來探望,剩下的繁瑣看護,就交給養老機構。
將母親送到養老院後,房女士終於騰出時間充分休息。她不必再6點多就從床上爬起來做飯,時時刻刻盯著母親,以免她摔倒受傷,她可以一覺睡到8點,再依著自己的口味準備餐食。生活重新握在自己手上。
 社區養老驛站里,一位老人正在看電影。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社區養老驛站里,一位老人正在看電影。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選擇養老機構:位置、價格與服務
突破觀念上的障礙、選擇進養老院後,另一堆複雜的問題又擺在了失能老人和家屬眼前。
在北京,目前備案的養老機構共有571家,床位總數11.2萬張,平均入住率僅為38.4%。失能老人想找到一家養老機構並不難,但匹配到合適的卻不簡單。它不僅是一張空床,還有背後配套的種種服務及設施,以及明碼標出的價格。
在北京市民政局相關科室負責人看來,老人不願意住進養老機構,主要原因之一是養老服務設施佈局與老年人需求存在空間錯配:「2/3以上養老機構及床位在郊區,但3/4以上老年人住在城區。老人更想就近養老,不願意入住偏遠的養老院。」
老人住在郊區,不便程度可想而知。曹瑤的母親住在密雲一家養老院,距曹瑤所住的朝陽區100多公里。每週,曹瑤需要花上兩三個小時坐車、再騎一個多小時電單車去探望母親。
心理諮詢師劉顥長期接觸失能老人,他注意到,很多老人寧願生活在市區10平方米的平房裡,也不願去郊區環境好的養老院。
除此之外,「錢」也是最為現實的影響因素。在今年5月發佈的北京市老年人居家養老服務需求調研報告(以下簡稱「調研報告」)中,參與調研的12.5萬名老年人里,22.9%的人在意價格高低。
北京市政協常委、市總工會黨組成員、副主席趙麗君曾在2021年提到,全市養老機構月均收費約5500元,重度失能失智老年人入住機構收費普遍在7000元以上,而多數老年人月均可支配收入在5000元左右。養老機構收費與老年人承受能力存在明顯差距。
調研報告也佐證了這一觀點。79.8%的老年人期望床位費控制在每月5000元以下,5000元-7000元的佔16.7%,只有不到4%的老人願意為養老床位每月支付8000元以上。
在養老機構從事4年照護工作的楊昆朋介紹,很多機構在看護失能老人方面,配有詳盡完備的服務和設施,譬如24小時值班的醫護人員,對失能老人進行用餐輔助、清潔照料、移動移程、二便護理、睡眠照護的護理人員,組織日常活動、進行心理陪伴的護工,準備營養三餐的廚師,以及康復設備和人員。
相應地,服務越周到、環境越適宜、地點越靠近城區,養老機構的收費也就越高昂,家庭要承擔的壓力也越大。
然而調研報告發現,子女對於花錢購買專業服務的消費習慣還未形成,僅兩成子女會給予老人補貼。可即便有子女幫扶,這也是一筆不小支出。
起初,曹瑤為母親選擇的養老照料中心每月需要4000多元。但算下來,自己一個月賺1萬多元,考慮到母親未來的醫藥費和喪葬費,每個月要存下薪金的五分之一,再去掉房租和養老院費用,她每個月留給自己的生活費不足3000元。
為了存下更多應付突髮狀況的錢,曹瑤將母親轉入了條件更簡陋、更便宜的養老院,每個月只需要2500元。可這樣的「低成本」養老,也意味著要犧牲不少生活質量。
盧淩峰每月要為重度失能、住在六人間的母親支付5000多元。母親是農村戶口,沒有退休金,父親是清潔工,每個月收入2000元。盧淩峰是家中獨子,每個月賺六七千元,這筆支出,已經佔家庭總收入的一大半,而這些還不包括醫藥費及尿不濕等費用。
北京市民政局相關科室負責人告訴記者,除去兜底保障項目和高端項目,北京大部分失能老人和家屬所關心的不是買不買得到服務,而是買不買得到普惠性的、優質的服務。
在周麗供職的養老機構,一名護理員需要照護4-5位老人,既包括半自理老人,也包括失能老人。家屬們都清楚,1對1的服務價格昂貴,差不多每天300元,普通家庭無法負擔,但來看望老人時,還是會囑咐周麗,多多關照老人,比如多洗幾次澡,或者多帶他們出去遛彎兒。
「家屬想要的屬於1對1服務,我們收費低,辦不到這些,只能對老人們一視同仁。」周麗說。
醫養結合:三成半老人在意醫療服務
失能老人和家屬在選擇養老機構時,生活照料是考慮的要素,同時醫療服務也不可或缺。
在調研報告中,針對「如何選擇養老機構」這一問題,35%的老年人最關注的是醫療設施是否完善。而一家彙集北京各養老機構的平台上,「提供醫療服務」也被作為「賣點」展示在首頁。
一篇發表在《中國衛生政策研究》論文提到,在北京,與非醫養結合養老機構相比,醫養結合養老機構的入住率高8.66個百分點。
「醫養結合」的概念起初在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發佈的《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年)》中得以明確。今年7月,國家醫保局表示,及時將「符合條件的養老機構內設醫療機構」納入醫保定點範圍,推進醫養結合發展。
一位失能老人家屬告訴記者,住在配有醫療設施、能為老人做些測量血壓等定期檢查、有醫生巡診的養老機構,確實比普通養老機構更令人放心。他重度失能的母親就曾住在這樣的養老機構里,每個月他會支付5000多元。老人想要享有吸氧、輸液等額外的、連續的醫療服務,需要按醫療收費標準單獨繳費。
對於部分癌症晚期、腦卒中等臥床的失能老人來說,連續的醫療服務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剛需。
唐蕾的父親長期臥床,日常護理需要用到尿管、鼻飼管、氧氣瓶,因為免疫力低下,還有隨時罹患肺炎的風險。
「在家和在養老院我們是沒有條件使用這些設備的,發生了肺炎也沒法馬上救治,但醫院又不讓我們長時間住。」眼下,唐蕾最迫切的需求就是既能讓父親有穩定的養老場所,又能給父親提供日常的醫療服務。可目前,市場上能提供完善、持續醫療服務的養老機構仍佔少數。
相關人士介紹,在北京市571家養老機構中,217家機構具備醫養結合條件,其中有8家「醫辦養」機構,即醫療機構開展養老服務,另有18家是兩個法人的「嵌入式」醫養結合。其餘190多家則是「養辦醫」,即養老機構設立或內設醫療體系,提供基本醫療服務。
有老人青睞「養辦醫」模式,但記者調查發現,有些養老機構雖然內設醫療機構,但會存在醫保報銷額度有限等問題。有的內設醫療機構只能處理日常慢病和健康管理,一旦老人出現重大疾病,還是會求助於醫院。
矛盾的是,目前大部分養老機構都在郊區,就不得不面臨醫療資源匱乏這一問題。
問題正在得到解決。北京市民政局相關科室負責人告訴記者,自疫情至今,北京市通過建立養老機構與醫療機構、120急救轉運、街道(鄉鎮)「三個握手」機制,開闢養老機構老年人就醫綠色通道,為老年人日常診療、非緊急就醫、急救轉運和日常用藥等提供保障,也增強了養老機構提供醫療服務的能力。
失能老人心理問題:被忽視的角落
對於失能老人家庭來說,為老人找到合適的養老服務,保障基本的生活需求已經不易,他們很容易忽視,老人也需要心理嗬護。
北京市社會心理聯合會副會長郭勇曾在2020年表示,中國老年人常常感到孤獨的佔人口總數的63%,存在抑鬱或焦慮症狀的佔22%。
「在人生最後、等待死亡到來的階段,老人們是無望的、恐懼的。他們身體會疼痛,在心理上也孤獨。」白蘭服務過幾百位老人,不少失能老人還會時不時地主動聯繫白蘭,不做別的,就是聊天——談論過去的美好生活,回憶還能自由活動的年輕歲月。
「他們接觸不到更多外界的人,有些子女也不常來探望,但他們渴望傾聽,渴望尊重,渴望愛的陪伴。」白蘭說,他們迫切地需要肯定——即使我失能了,但我的存在仍有意義,我是被歡迎的,不是被嫌棄的。
對此,他們中的許多人表現為渴求關注,另一些則需要對生活和自身仍有掌控感。這在房女士母親所在的養老機構尤為明顯。有的老人沒事就按鈴呼叫;有的老人,就像房女士的母親,很少主動呼叫護理員服務。為了方便她喝酸奶,護理員會將她的床頭升起來,一勺一勺喂給她。她會擺擺乾瘦的手臂,示意等下自己來。
他們心裡希望後輩多來看看自己,但又不停地表示理解:「孩子們都忙,我們在這,他們也省心。」還有人不斷回味居家時的生活,想再次回到熟悉的地方。一些被強行送入養老機構的失能老人,就會變得自閉——把門插上,不再接觸外界。
在白蘭服務過的失能老人中,死亡是談論最多的話題。但這些人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夠坦然地面對死亡,準備好壽服、交待後事,剩下大部分人常常帶著種種情緒,說「還不如死了」。
「這就說明他們還是渴望生存,渴望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白蘭說,剩下一大部分老人則迴避死亡。「他們害怕,認為還不該到這一階段,有的人表現出來的是憤怒,有的會抑鬱。」
白蘭覺得,對待失能老人,不只要對他們的身體細緻嗬護,還要在精神上給予關照。不論是個人還是養老機構,都應該努力讓老人們接納衰老、接納殘缺。
特別是養老服務機構,除了做好養老服務之外,還應重視心理關懷及情緒疏導等方面內容。但2020年舉行的北京市社會心理工作聯合會老年心理專業委員會成立及工作研討會提到,很多養老服務機構因為種種原因並未開展專業化的心理健康關愛活動。
北京市民政局二級巡視員、北京市社會心理工作聯合會會長張青之表示,養老服務機構等更需要引入專業人才和心理服務,如此才能為空巢、失能、失智、留守等老人提供更及時的心理支持、心理康復等服務,從而健全政府、社會、家庭「三位一體」的幫扶體系。
 老人正在理髮。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老人正在理髮。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北京市民政局相關科室負責人告訴記者,在5月份調研報告中,老人們除了關心醫療設施、區域位置等,也關心老年活動,希望有更快樂的晚年,而不是在陌生的機構中「等死」。
很多養老機構考慮到了這一點。劉芳說,他們居家時,老伴兒為數不多的娛樂活動就是看電視,但到了養老服務驛站,他可以跟其他老人聊天,逢年過節還會做手工、包粽子,生活不再單調枯燥。
房女士的母親也是幸運的。
他們選定的養老照料中心距離自家步行只要六七分鐘,有時房女士懶得做飯,就到中心來,跟母親一起在餐廳用餐。房間里居住的都是附近鄰居,彼此也聊得來。房女士有時會問母親:你還想回家嗎?母親會告訴她:「這裏挺好,我哪也不去了。」
在桑治莊一家高端養老社區,兩戶老人也都說出同樣的話。他們因為衰老,離開熟悉的家,來到陌生的新「家」。或許這裏就是他們的最終歸宿了。
(文中除白蘭、楊昆朋、周麗外,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史航 左琳 實習生 桑治漪靜
編輯 楊海 校對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