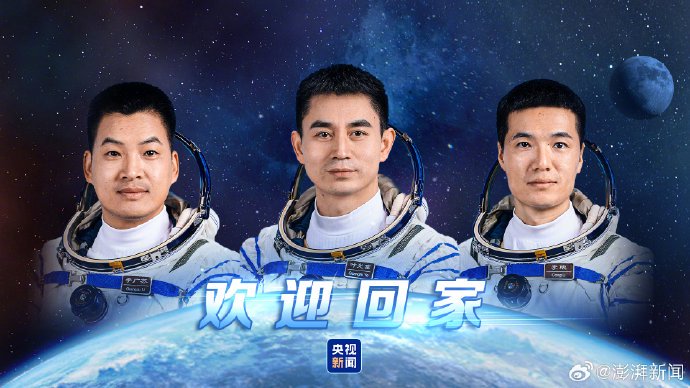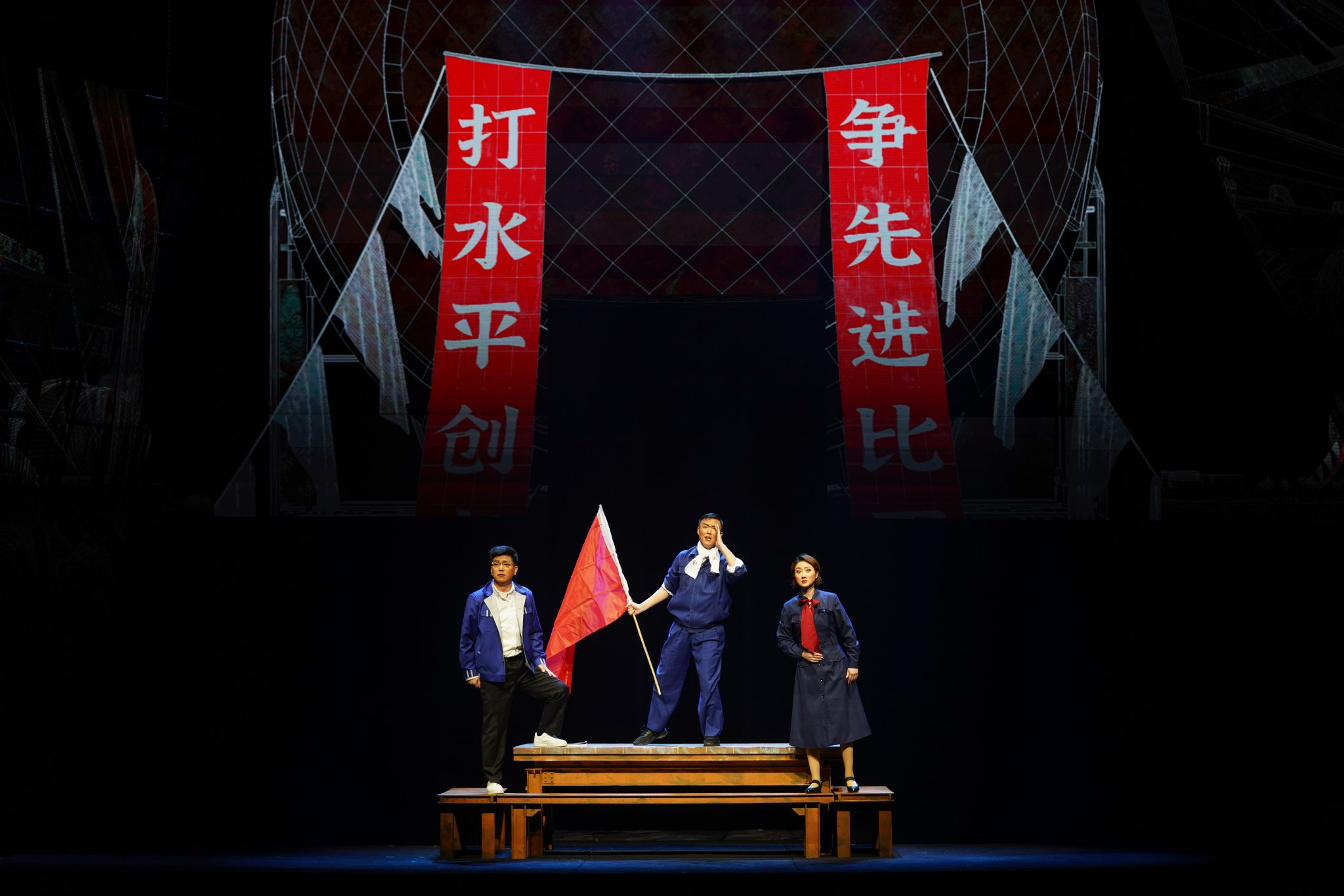盛海琳,一個人的戰鬥

11:17
60歲失獨再生育,74歲託孤失敗。盛海琳相信,只要沒進墳墓,就要解決迎面而來的問題。澎湃新聞記者 何鍇 葛明寧 視頻編輯 吳佳穎 調色 江勇 後期 鬱斐(11:17)
人到晚年,盛海琳突遭許多變故。
她的世界一度回到了“對”的狀態,破碎的家庭好不容易完整了。這一家子人,有爸爸媽媽,兩個孩子,有體面的生活,最多的時候,家裡用三個保姆。
2009年,盛海琳的大女兒意外去世。人到59歲,失獨的她拚了命做“試管嬰兒”,生下一對雙胞胎姊妹。後來她一度到處講課,想賺更多錢供養年幼的孩子。
這光景又像泡沫一樣破滅——2022年底,她的丈夫走了。她重新算一算賬,兩人將近三萬元的退休金收入縮到一萬以內。她的“老本”寄存在乾妹妹陳曉雲那裡,對方是兩個孩子的“北京媽媽”,這些年兩人走得很近。盛海琳想問她要回錢,對方卻不給,她無奈去向警方報案。
深感被人欺騙,盛海琳沒辦法爽快地走出這痛苦的圓圈:通常是晚上十點,她吃過安眠藥,躺在床上,淩晨一點入睡,兩點驚醒,輾轉反側,四點再朦朧睡去。
如今她沒有一個可依靠的肩膀,但對於“孤獨”的評價,卻絲毫不認同,“我是勇者”,她糾正說。她相信,只要沒進墳墓,就只能逐次解決迎面而來的問題。
 盛海琳 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何鍇 攝
盛海琳 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何鍇 攝“年輕人的世界”
盛海琳要去治牙,打了兩輛出租車去醫院。她的身邊沒有兄弟姐妹,也沒有侄子、侄女,他們全有自己的生活。陪她去的是兩個十三歲的女兒、一個朋友、她直播帶貨團隊里負責短視頻拍攝的女孩,和我們。這一天,她戴著紅綠拚色耳環,腳蹬三四公分的中跟鞋,漂漂亮亮的。
她是一個慣於講究生活的人,有什麼新技術出來,都想嚐試一下,這些年,陸續種了四顆牙。她還牙齦出血,自己解釋,一個是生完兩個小女兒後骨質疏鬆,一個是愛嗑瓜子,嗑大了牙縫。她有時候提起高齡生育得了什麼病,又會想起來,女兒會不高興,她們提過“老是講,媽媽你把我們搞回肚子裡去”。
這幾個月,因為經濟困頓,盛海琳睡不著覺,牙齦都腫起來,“每天早上吐一口血”。
她手頭緊,對拍視頻很上心。前一天,她打電話給這傢俬立的牙科醫院預約掛號,說要帶人去拍攝:“小丫頭嚇得說要和領導請示,我說,請示什麼,我是你們的代言人,你知道吧?”
那是五六年前的事,盛海琳因為高齡產子,出了名,合肥到處掛著她露齒而笑的照片。她給牙科醫院拍這一套廣告,種牙的費用就給打了折。
她說,自己的個性是遺傳爸爸,爸爸是知識分子、部隊里的軍官。盛海琳總是自然而然地提起來,小時候,爸爸出去做講座會帶著她,她是家裡老大。她的爸爸有學識、有風度,一呼百應,她跟著學會了怎麼說話、表現自己。爸爸的樣子一直伴隨著她。
可到了門診大廳,戴著工牌的“諮詢主管”不讓幾波跟拍她的人同去診室,說她聯繫的只是客服,客服不算數。
“你們當時需要我宣傳,現在用不著了,把我踢到門外頭了,是不是?”她急得說。
盛海琳愛漂亮、覺得人越老越該打扮,她看見,在她最近的直播里,很多同情的留言之間,也有人說:“孩子的爸爸都不在了,你搞這麼漂亮,給誰看呢?”
直播帶貨的時候,提起再婚,還有人留言說,“沒人會要你的,你太厲害”。
在她的回憶里,生兩個小女兒的時候,很少有人支持她,別人說:“你和孩子相差六十歲,老兩口死掉怎麼辦?”
盛海琳從前是朋輩之間活得好的,在部隊大院里,父親軍銜高,她找的丈夫也是部隊里的人,幾十年來錢都給她。失獨再生育後她搞直播帶貨,認識了一些“失獨”家庭。他們到她家裡來聚,會說起孩子走了,有的親戚想把成年的子女“過繼”給他們,覬覦他們的錢。這樣的家庭感到孤立無助。

盛海琳的直播間
當初,盛海琳堅持要再次懷孕,大著肚子在醫院里,等著剖腹產,她托朋友給自己買一樣東西,朋友沒有給她找零。她不好意思開口要,又變得更加傷感,想著“現在已經是沒有錢成不了事了”。
據她說,後來為了照顧身體不好的丈夫、兩個孩子,“請過八十多個保姆”,多數她也不喜歡,放心不下。她稱,有保姆趁她出門搞醫學講座,把男朋友帶回她的家,又偷走她儲存的火腿。
在她眼裡,其他老人有飽滿的生活,她的那些朋友,有兒子、有孫子、有幾套房,有的離婚或者喪偶,也落寞了一段時間,又找到了新的老伴。他們與她“不在一個頻道上”。而年輕人們在她周圍來來去去,他們的世界,她也走不進去。
45年婚姻
丈夫死去之後,盛海琳才感受到他對她的愛。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是軍事學院的教授,工資比她高。盛海琳花錢買東西、打扮,他從來不管;她接濟娘家的親戚,他沒有怨言。
但在她看來,他雖不吭聲,卻需要她關注很多瑣瑣碎碎的東西,要嘮叨他,管著他,讓他別老吃剩菜,少喝酒——上了年紀之後,丈夫冒出了心肌梗死、糖尿病、高血壓、腦中風、肝脾腫大等問題,加劇家庭矛盾。說他太多次,他調侃地說:“我找一個醫生老婆是幹什麼呢?”她氣極了,說反話:“你可考慮到我的感受了。”
現在,他長眠在早逝的大女兒瑩瑩身邊,徹底陷入了沉默。

盛海琳帶著兩個女兒去墓地
他從前和她分房睡,兩個人的臥室對著門,盛海琳覺得他“像鄰居”。他一輩子,吃喝隨便,喝酒很多,與她沒有什麼共同語言;他在外的形象溫文爾雅,對同事、學生都很和善,但在她眼裡,有些過於和善了。盛海琳總是抓到他給瑩瑩寫作業,自己做好了,給她抄。後來瑩瑩的學業表現不夠好,她認為跟丈夫的教育有關。
上世紀七十年代,她去離退休幹部居住的干休所找朋友玩——干休所“鳥語花香”,退休的老紅軍閑不住,養雞養鴨、開魚塘,干休所的戰士把一大片空地都開了荒,種黃澄澄的油菜,家家戶戶能分到油;她的朋友非要拉她去自己表叔家裡。那位長輩很喜歡她,第二年春節,安排她和自己在部隊的大兒子見面。
當時在部隊里,追求與戀愛都是公開的,盛海琳工作醫院的領導找她談話、做她工作。她年紀不小,也不想找比自己更年輕的人,兩個人就結婚了。
認識這對夫妻的人,都覺得男方性格偏軟: “所有人都說我欺負他。”
兩人無話可說,丈夫卻又非常“黏糊”,老大年紀,會突然過來摸摸她的頭,盛海琳說:“幹什麼?”落下一身的雞皮疙瘩;她剛退休時,喜歡晚上跳舞,丈夫吃醋,開玩笑說,要搞一個棗木棍子打斷她的腿。
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她人能幹,又在部隊大院里長大,認得很多人,有人想拉她一道,在合肥籌措資金,到海南去創業。她非常動心,但她丈夫反對,不想讓她去。
盛海琳罕見地沒有抗議,她自己也不想看著這個家散了。她去南京的醫院進修,對方想留她下來,她也沒幹,想著丈夫剛從南京調回合肥,她要回合肥與家人團聚。
女兒瑩瑩長大了,是一個學業一般、個性軟糯的女孩。盛海琳擔憂女兒嫁到一個幹部家庭,被公公婆婆拿捏住,所以,支持她和一個家境普通、在她眼裡有點寒微的人在一起。臨到結婚,鬧得一地雞毛。盛海琳花大錢給女兒在合肥買房、裝修,男方父母感到抹不開面子,埋怨她把掏錢買房的事情說開,又說,生下孩子要交給他們帶。盛海琳想,反正小夫妻兩個住在合肥,他爹娘要來帶孩子,也要過來合肥帶,能出什麼差錯?
結婚以後,女兒去男方老家小住,沒想到這對新人意外死於煤氣中毒。
那段時間,盛海琳常思考著,自己“身體好得不得了”,往後還有很多年要活,漫漫無期,可想像的全是恨、痛苦、懷念;要是出去旅遊,她看到漂亮衣服,想到死去的女兒穿會漂亮,看到熱帶水果,想到女兒會喜歡吃……這種生活是煎熬,簡直無法可想。
她想再生個孩子。為此,她忍受了身體上極大的苦楚,在將近六十歲時靠“試管嬰兒”誕下兩個女兒。
“北京媽媽”
12年後,兩個女兒剛上初中,盛海琳在醫院急診簽了丈夫的“病危通知書”,這是2022年12月4日,一個週日。
她說,雖然丈夫當初不支持再次生育,真有了兩個孩子,他也非常喜歡。這天一早,彷彿有預感一般,他到她們的房間里,看她倆在床上吃早飯。然後跟她們握手,跟大的握完了,跟小的握。盛海琳看著覺得有些奇怪。

丈夫生前與盛海琳及雙胞胎女兒的合照
下午,她正在準備孩子們回寄宿製學校的東西,忙得焦頭爛額,丈夫說心臟不舒服,於是,打120送醫院。“病危通知書”這樣東西,她以前也為丈夫簽過,進了急診部,問了是心臟問題,給她遞上來這份兩頁的文件,載明了各種各樣“為贏得更多搶救時間”可能進行的治療,包括氣管插管。她簽了字,覺得要是真插管,肯定還要再簽。
等做完核酸,丈夫就被送進重症監護室,盛海琳要回家繼續給孩子收拾行李;醫院給她打電話,說血氧飽和度低,要插管。盛海琳記得自己說,不能插管,要自己看過,聽到丈夫在背景音里說自己餓,要吃包子。
在她印象里,又過了20分鍾,第二個電話打來,說丈夫呼吸停止。她倉促趕到了醫院,看見他們給丈夫做了氣管插管,這時候,他心律紊亂,心律失常,瞳孔散大——盛海琳以前寫過一篇瀕死症狀的論文,為了寫它,在病房裡看了將近一天。她很熟悉這一條路。她喊丈夫名字,他的喉嚨里發出辨認不清的音節,“說明他的魂還沒走,你別不相信”,她後來回想時對我們說。
丈夫死後,她一定要和醫院打官司,說打了才能讓自己心安。
律師看見這份冗長的同意書,問她:“這是你的字嗎?”
盛海琳疑惑地說,一點印象也沒有了,而且不該插管的時候再簽一次?

盛海琳在墓前哭泣

丈夫的墓碑
盛海琳近半年陷入了嚴重的不安全感。她對我們說過幾次,“我要掙錢”,她硬著口吻說,這些年的捶打已經讓她變了個人。盛海琳掙錢的目的之一是請兩個保鏢保護她。她想,大女兒與丈夫都是意外亡故的,她一定要小心謹慎,她怕與醫院打官司也許會得罪什麼人。
另一方面,她還身陷於與陳曉雲(化名)的“友情”之中。按照盛海琳的說法,2017年,陳曉雲打電話到大女兒瑩瑩生前的工作單位,說想要認識她。兩人加上微信之後,她先自稱是北京301醫院的醫生,想幫助盛海琳,介紹她一起參與一種保健產品推銷。
據盛海琳的回憶,陳曉雲當時自稱1958年出生,是“紅二代”。
目前擔任盛海琳直播間運營的餘升說,記得盛的丈夫說過一句,陳曉雲像個騙子。
但是,盛海琳說:“每一回我生病,孩子的爸爸生病,她(指陳曉雲)能及時出現,我們無力的時候她搭一把手,甚至自己貼上路費,還買了東西在後頭跟著,你說我能不感動?”
盛海琳所說的推銷保健品指的是由保健品公司讚助,到各地做一些醫學講座。她自稱只收取講課費用。
不過,她也提到,有社交平台直播間里認識的粉絲找她諮詢,她會推薦醫生、醫院,也會介紹些購買保健品的渠道,有的一套價格上萬。據查詢,她提及的一種保健品由美國生產,自稱是“直銷企業”的這家廠家介紹,上述保健品屬於膳食補充劑。
大女兒還在世的時候,盛海琳也參與一些這樣的活動,她樂意做,感到可以豐富晚年生活。等到兩個小女兒出生,請保姆的經濟壓力驟然加大,她開始不停地接這樣的工作,總是飛來飛去。盛海琳的拉杆箱用壞了不下十個,陳曉雲給她買了一個進口的,又輕便,又結實耐用。
說起帶兩個孩子有多麼難,“還沒有出月子的時候,”盛海琳說,“鬧得我精神恍惚了。”她覺得自己得了產後抑鬱症,有想把孩子扔了的念頭。盛海琳沒學會網購之前,只會在出差經過的機場里給孩子買衣服,價格奇高,而她認識陳曉雲之後,對方一直給兩個孩子寄吃的、寄穿的。
盛海琳回憶,在認識兩年之後,陳曉雲對她說,丈夫的工作單位有一個內部“小金庫”,專門搞採購,可以投資掙一些利潤。盛海琳陸陸續續打了約190萬元給她。
“託孤”
丈夫去世之後,盛海琳失去他的退休金,急用錢,她給我們看了一些聊天記錄——微信“轟炸”陳曉雲,討要“老本”,對方拖延著,說自己遇到了麻煩。
麻煩來得不止這一項。2021年,盛海琳試水做直播帶貨,拉了粉絲團。一些“失獨”和因為其他原因大齡求子的人找到她,提著牛奶,哭訴著他們心中的痛苦。她留他們吃飯,最多的時候,一個月吃掉七八十斤米。盛海琳甚至買了第二個冰箱:“每次大概要七八個菜,不能不吃好,對不對?”
她說,陳曉雲認為她身邊的年輕人不可靠,要求自己來當她的助理。有幾年時間,加入盛海琳的粉絲團,就會在群裡收到陳曉雲的電話號碼。盛海琳說,陳曉雲沒和自己商量,就向這些粉絲推銷保健品,有時候收了錢不發貨,還寄出一些按規定只能憑處方購買的藥物,把人吃出病來。
一些想要生育的人,為了孩子“多少錢都付得出”,從陳曉雲這裏獲得不了允諾的服務,2022年上半年,他們陸續找盛海琳理論,搬出醫生的姓名,才發現是治風濕病的;三方爭執之下,陳曉雲陸續退了以各種名目收取的五個客戶的資金。
今年5月,在朋友的勸說下,盛海琳選擇了報警。7月,合肥市公安局給盛海琳短信回覆稱,公安部門已對陳曉雲進行刑事立案偵查。記者想瞭解案件進展,但截至發稿前,辦案警官的電話始終無人接聽。
陳曉雲的短視頻賬號一度與盛海琳的密切互動,現在,她把自己露臉的視頻都刪光了,只留下盛海琳與雙胞胎女兒的影像。盛海琳想來想去,也發現,交往六年,一張陳曉雲的照片也沒有。
盛海琳剛認識陳曉雲的時候,她的雙胞胎女兒才七八歲。盛海琳解釋,如此信任陳曉雲,原因之一是急於“託孤”。
剛生下孩子,盛海琳就要出門講課掙錢,丈夫也帶不動孩子,兩個孩子一歲零四個月,就送去了親子園,晚上由保姆接回家。她們給盛海琳打電話,哭,盛海琳硬著心腸說:“媽媽要掙錢養寶寶,沒有錢你們沒奶粉喝,知道嗎?”
晚上,盛海琳多付給鍾點工一些錢,讓七點走,孩子們正是跑動能力很強的年紀,而她快七十了。“我腿都邁不動。”她說。
兩個孩子要一起去買東西,回家路上,盛海琳就讓女兒拎牛奶,趁機會教育一下。她說:“你們的媽媽和別的媽媽有什麼不同?”
孩子們有的說媽媽會講課,有的說媽媽漂亮,盛海琳正色道:“不對。”她倆只好老實說:“媽媽很老。”
“你們可能沒辦法理解。”盛海琳講,大女兒死去之後,她信了佛,也求過佛再給自己孩子,雙胞胎生出來三個月,她抱著大的喊出了大女兒的名字,新生兒流了眼淚,她也抓著機會對孩子說:“你是姐姐,妹妹生下來才兩斤,將來爸爸媽媽年齡大了,老了,這個家就靠你當了,你是我們家庭的支柱。”
一直都是盛海琳一個人想再要孩子,她說“做母親是快樂的”,這種快樂在她頭腦中特別具象——大女兒小時候是多麼可愛,牽出去“被誇一路”,孩子還不會表達的時候,想喝水就張著嘴吮吸,餓了就拍拍肚子——其實,大女兒意外辭世的時候,盛海琳的婆家和娘家都有其他孫輩,不大在意後代,她丈夫也不想再生。盛海琳跪下來磕頭,丈夫才答應做試管,說:“那你也別再管我喝酒。”
在子宮里種下兩個胚胎之後,她渾身浮腫、挑食、喉嚨里冒酸水,因為怕流產,大小便都不敢使勁。丈夫晚上總喝酒,悲傷也喝,高興也喝,喝完就睡得很死,她自己給自己弄早飯、煮雞蛋。
有了孩子以後,家務事太吵,丈夫有時候抱怨,她說:“你別埋怨我。我又沒要你幫忙。”
盛海琳還要丈夫保證,不再管孩子的教育,可是,在她看來,雙胞胎還是有點兒內向。盛海琳武斷地認為,這沒辦法,女兒的個性總是像爸爸。
她心態有點矛盾。盛海琳覺得“黏糊”不好,可看下來,在外明顯是丈夫的人緣比她這個外向、活潑的人更強。他突然去世,同學們嘩嘩地上門,還捐了很多錢;而她孤家寡人,這些年拖著孩子,沒什麼人慰問。
同一種語言
結束了兩個小時的帶貨直播,盛海琳需要睡一下。
她在直播中說,自己現在“老臉也丟光了,老公也沒了,老米(指錢)也沒有了”。
她不喜歡吃安眠藥,從前開過一些,都吃不完,還是她丈夫給她攢下這些藥片。從前兩人看電視都看不到一起,他要看時事新聞,她要看電視劇,總是分兩處看。他死去之後,客廳里的電視機再沒打開過。
現在,她覺得客廳靜得可怕,她想說話也沒有了回音。
她平日在直播間里,對著雪亮的反光燈,叫賣抽紙、不到十元一包的預製菜。從前她和丈夫兩人的退休金,一大半被她“剁手”沒了,她也不覺得自己的大手大腳是個錯,買得不好的衣服可以找裁縫改,要不送給兩個孩子的老師、保姆,反正,總有一個用處;現在她窘迫了,直播間里展示過的預製菜要留,助播小女生給她端回家,家裡的兩個女孩在青春期,喜歡吃油的、口味重的,她們其實動手能力挺強,有時候拿直播間里帶回的螺螄粉來煮,盛海琳也不管。
盛海琳倒是從來不糾結自己怎麼養老的問題。她覺得,不行就去一個每月費用四千元的養老院與舊相識搭伴兒,四千塊錢也可以過得很好。
失去大女兒之後,她拚死生育,想的不是“養兒防老”這一回事,兩個小女兒跟她差60歲,實在太小了。說起來,指望兒女報恩是不可靠的,她去外地搞醫學講座,還有聽眾里的老年人訴苦,說被自己的孩子們“搜刮”得沒什麼錢。
她現在的“合夥人”餘升在辦公室里接待了我。他不到三十歲,幾年前他給盛海琳當直播運營,輕易地被陳曉雲打發走了,這幾個月又回來幹。
他說,盛海琳是一個很孤獨的人,她手裡一度有一筆數額可觀的錢,於是,很多人迎上來,有人讓她做外貿、做期貨。
餘升接手了盛海琳的帶貨直播,做得不順,一開始,也考慮以賣保健品為主,但發現她收不住,一講起醫學知識就滔滔不絕,容易被平台判為違規、進而封號。他們得陪著小心對盛海琳講這些,對於一個老年人,“不能教她做什麼, 只能幽默地引導一下”,她有自己的價值觀、世界觀。
與盛海琳待得多了,會聽到她提起錯過的發財機會。餘升剛出來自己單干,感覺挺開眼界。
今年五月,盛海琳給他打電話,說感到自己被陳曉雲騙了。他去見她,她手腕上還紮著輸液用的塑料帶。盛海琳一直哭。
餘升聽了情況,想了想,問她:“陳曉雲給這些在後台聚集起來想生育的人介紹醫院,你掙過差價嗎?”盛海琳堅稱,從來沒有。
餘升說,他相信盛海琳:盛老師是個好人,對兩個女兒也很關照、很用心。
他覺得盛海琳不可能往這些與自己同病相憐的人身上撈錢,但是,現在看後台希望盛海琳介紹醫院的網友還在增加,都很熱切,他也在思忖,要不要掙一點中介費。但餘升坦言自己並不懂醫藥。
即便是盛海琳在網上自曝遇著了“陳騙子”,她家裡的客人還是絡繹不絕。除了高齡喪子的,盛海琳也接待一些大齡未婚的。
她對我們背了自己印象里的劉曉慶語錄:“婚姻是個桎梏,是扼殺人性的,男女願意好就好,生了孩子一人一半……”但她說,這不是自己心中所想。
頻繁地見網友,盛海琳還會捲入一些新的難辨真假的故事里,一些高齡未婚的,帶自己的男朋友上門,兩人又不像正經關係,盛海琳不明白;現在陳曉雲不見了,她會讓家裡的保姆陪他們上醫院找她自己看過的醫生、給他們寄藥……
盛海琳說,再不想找哪個人“託孤”,只希望自己好好活著。
但她又說,有一些高齡喪子、又生育的,他們是一個想被看見的群體,使用同一種痛苦的語言。他們是一家人。

盛海琳和兩個女兒在等車
(文中陳曉雲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