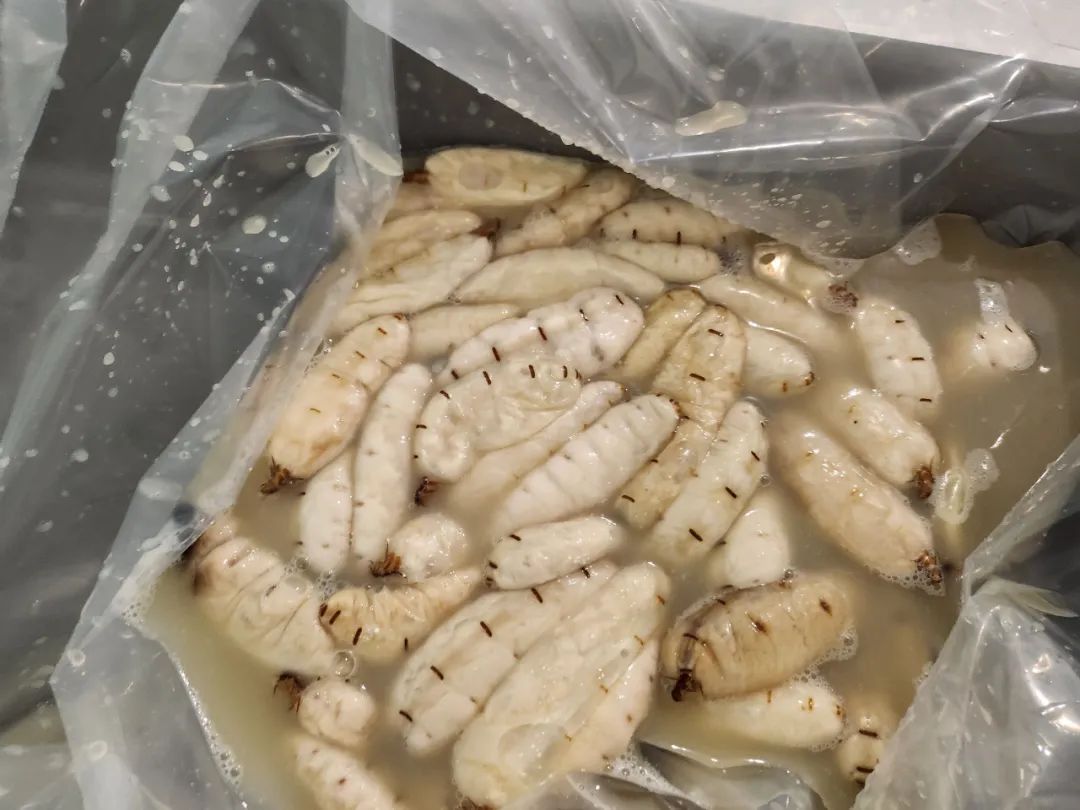話劇《鱷魚》導演王可然:用悲憫和魔幻展示每人都是慾望之「鱷」

話劇《鱷魚》巡演足跡遍及全國16座城市。
由莫言編劇、王可然導演的話劇《鱷魚》於9月1日在北京保利劇院收官。《鱷魚》巡演足跡遍及全國16座城市,總場次多達36場,實現了口碑美譽度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在多個城市問鼎嚴肅戲劇的票房冠軍。日前,該劇導演王可然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自己第一次看完《鱷魚》的劇本,腦子是蒙的;第二遍看的時候,他帶入了自己的感情,看到一半就哭了,觸動特別大,「我一下感覺無法呼吸了。《鱷魚》中每一個人都是我身邊的人,都是我見過的人,他們切實地構成了我生活的洪流。」
【劇作特點】
莫言的原著充滿救贖和悲憫的力量
《鱷魚》是作家莫言在獲得盧保文學獎後,於2023年推出的首部長篇話劇劇作。故事圍繞外逃的反派主人公單無憚,及其在生日派對上收到的賀禮「鱷魚」展開,通過一條無限生長、會說話的鱷魚,挖掘人性深處的秘密。作品融合了大量精彩對白,以及富於想像力的戲劇衝突設計,加之獨具特色的「莫言式魔幻」,呈現了「人性和慾望的複雜性」。

《鱷魚》整部作品都充滿了救贖和悲憫的力量。
《鱷魚》中的每個主要人物都在用偽善來偽裝自己的慾望,比如貪婪腐化、同時又頗具文人氣質的逃亡市長單無憚;單無憚狡詐虛偽的 「親戚」牛不;阿諛奉承、依附於權貴的「寄生蟲」市長秘書劉慕飛。他們口中滿是道理和情義,可是做的卻都是最殘酷的事。這也是王可然喜歡莫言作品的原因,對人物有著豐厚的刻畫,整部作品都充滿了救贖和悲憫的力量。
《鱷魚》的籌備期在央華所有的戲劇創作里都是最短的,只有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其中完整集中的排練和舞台呈現創作時間只有一個多月。而一部如此大體量的戲劇,通常的籌備期都是準備兩年,最少也是一年。王可然坦言,時間短就意味著,要求團隊克服各種困難,以及作為導演要面對戲劇構架設計、創作思路等一系列問題;還包括在準備過程中,和創作團隊在各種細節上的磨合、認知的建立、方案的設定和認同等。同時,《鱷魚》所涉及的創作、製作等方面很複雜,它是一部龐大的戲劇,「如何在‘龐大’中建立有條理的規則是一個巨大的壓力來源。」
【改編區別】
舞台與劇本是不一樣的節奏
《鱷魚》在今年3月進入正式排練,從5月3日在蘇州開始的全國首演到9月1日的收官演出,足跡遍及全國16座城市,總場次多達36場。王可然表示,當《鱷魚》被搬上舞台以後,這個句號不是導演畫的,而是觀眾畫的,所以絕大部分的觀眾滿意,他才能夠稱之為滿意。王可然曾經做過統計,在全劇三個小時的時長中,出現了三四十次笑聲,他和團隊也會根據每一站巡演的現場反饋,不斷在做調整,團隊每隔兩站都做一次新的創作以及排練,不僅是因為要根據線下的反饋,而是大家心裡很清楚,這部作品還沒有做到完美的程度。

莫言(左四)與話劇《鱷魚》眾位主創向觀眾致意。
作為原創和改編者,莫言是《鱷魚》文本的建設者和創作者,《鱷魚》的舞台呈現在文本上幾乎沒有改編,是嚴格按照莫言的劇本來排演的。在王可然看來,莫言寫得非常棒,他認為沒有需要改的地方。但是,即便是同一部《鱷魚》,舞台與劇本的節奏其實也是不一樣的,在文本的閱讀中,每一個讀者都有個人的想像力空間,和文字表現力的「留白空間」不同,舞台不會在當時當刻給觀眾留下想像的時間,觀眾更多是在看完了之後再去回味、想像。看戲劇是享受地看,看文字的人是想像著看,這是兩種想像力。」

導演王可然(圖中)在話劇《鱷魚》排練現場。
在王可然看來,他能努力做到的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尊重觀眾的喜好,搭建出一部大戲,而戲劇的獨特魅力也恰恰源自其劇場性,這是影視作品的呈現所不具有的。「只有在劇場才能夠構建出人對於過去和此刻的夢境,這個夢境是獨一無二的。」
【主題意象】
每個人都是慾望之「鱷」
「鱷魚」無疑是這部作品的主體意象,一條黑色、龐大的鱷魚幾乎從頭到尾霸佔著舞檯布景的中央位置,它同樣也是戲劇主題意象,充滿著不可遏製的不斷膨脹的慾望,也是人性貪婪的象徵。單無憚在海外家庭崩裂、情人跟他的秘書出走、兒子吸毒自殺、自己葬身鱷魚腹中的命運主線也都圍繞著「鱷魚」一一展開。王可然表示,「每個人都是鱷魚,只是看要不要把慾望飼養到可以吞噬自己的程度。」

一條黑色、龐大的鱷魚幾乎從頭到尾霸佔著舞檯布景的中央位置。
《鱷魚》是一部魔幻現實主義作品,文本有豐富的想像空間,作為更為具象化的舞台藝術應該如何去呈現這部劇的魔幻風格?對此,王可然坦言,其中的方法很多,核心就是要讓觀眾在不知不覺中、舒適地接受這種魔幻。一切舞台手段都讓觀眾感受到每一個人都是慾望之「鱷」,向光而不得。暗綠色的佈景、鱷魚形的沙發與舞台上巨大的「鱷魚」背景融為一體,觀眾從看舞台上的「鱷魚」逐漸感受到整個舞台就是「鱷魚池」,每一個人物都是「大鱷」,更是慾望的奴隸。
舞台上呈現的是主人公單無憚走向鱷魚,和它合二為一,最後單無憚被鱷魚吞噬、毀滅,而在另一方面,劇中的所有人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不同的鱷魚,關鍵是能不能控制住自己內心的慾望。作為一個戲劇工作者,王可然表示,自己的任務就是把「鱷魚」呈現在舞台上,讓觀眾自己去理解、消化。
【舞台細節】用手電筒照亮演員和觀眾的內心
在舞台呈現的具體表達上,王可然還在劇本基礎上,創造出了一組表現「靈魂」的人物。演出現場有不少觀眾發現,劇中提到「瘦馬」墮胎失去了三個孩子,但卻總有四個青年演員跟隨自殺的「小濤」一起「靈魂遊蕩」。王可然表示,他刻意不只用三個演員,就是因為他們代表的不僅是單無憚死去的孩子們,還是象徵所有被慾望所吞噬掉的青春和生命。

話劇《鱷魚》劇照。 用「靈魂」象徵所有被慾望所吞噬掉的青春和生命。
《鱷魚》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場戲可以算是全劇結尾,最後趙文瑄飾演的單無憚奉獻了一大段長達12分鐘的獨白。王可然用了各種處理方式來加強這場戲的表達,比如身處在劇場通道的演員們拿手電光「逼視」觀眾的眼睛,演員們從觀眾席中登台,在觀眾身邊表演;用手電筒照射舞台上的單無憚,也將光束射向觀眾,彷彿也在提醒著觀眾,難以有人可以在此置身事外,此時整個劇場都變成了舞台,從單無憚身上看到「鱷魚」,也看到自我。在王可然看來,雖然手電筒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工具,可是用這樣一個小小的動作,可以把整場觀眾和演員的內心照亮,把窺探慾望的情緒拉滿,這就是劇場性一個極小的微不足道的細節表現,「不需要用複雜的技術,用好的技法才能構建複雜的情感與情緒。」
王可然說,他不喜歡黑暗戲劇。拿著手電筒互相照向對方的時候,王可然希望在劇場里每個人都在被照。「這部作品最後的表達是悲憫,並不是黑暗。」
【主演選擇】
主人公要帶給觀眾想像空間,趙文瑄的感覺一下就對了
《鱷魚》中的主人公單無憚曾經是風光一時的市長,後因為貪汙逃亡到海外,他中文系出身,滿身書卷氣,但又是一個極為貪婪的人,他對於拋棄糟糠之妻毫無內疚,依舊能理直氣壯面對妻子的質詢,雖然背負著巨額貪汙,他依舊滿口仁義道德,毫無悔意,與週遭的各色人物打交道都應對自如。單無憚在劇中的戲份巨大,而單無憚這個人物塑造是否成功,也直接影響到這部作品的成敗。

趙文瑄在話劇《鱷魚》中飾演主人公單無憚,他是所有被慾望吞噬的人的縮影。
原本可以來演繹單無憚的演員人選很多,但王可然不想呈現一個傳統印象中的市長,他不希望讓觀眾有先入為主的概念,而是帶給觀眾一定的想像空間。在王可然看來,單無憚是所有被慾望吞噬的人的縮影,他的身份不僅僅局限在官員,可以是商人,也可以是學閥。「我不願意選一個一看就知道是其中某一種類型的演員。」
直到某天淩晨兩三點,王可然在入睡前隨手刷著短影片,他突然刷到了一條趙文瑄在家裡逗小動物的影片,在大家印象中,趙文瑄是「美男子」人設,此前很少有人把他和「外逃市長」聯繫在一起。在短影片中的趙文瑄天然具有書卷氣,但是他又一點不顧及形象。感覺一下就對了。王可然馬上讓同事去聯繫了趙文瑄,「我說趕快給我找他。」
【人物塑造】
凱麗和丹恩萃雯角色「核心的戲劇衝突就是對抗」
女演員方面,最先定下來的是飾演單無憚妻子巧玲的凱麗,也正因此,王可然堅持,作為「情敵」的瘦馬,演員人選氣質一定要和凱麗有區分。王可然坦言,瘦馬其實可以選擇的演員也很多,但是劇中單無憚那麼抗拒自己的原配,他將心中的慾望投射到另一個女人身上,這必然是完全不相同的兩個女人,「兩人核心的戲劇衝突就是對抗,巧玲和瘦馬是兩個極聰明的女性在對抗。」王可然在和朋友吃飯時,偶然聽朋友提到丹恩萃雯,此前他沒有看過丹恩萃雯的任何一部作品,他說,給我看看丹恩萃雯的照片。看完照片他就問,能不能幫我請她來演瘦馬?王可然並不擔心丹恩萃雯的「港普」,「劇本中故事的背景是濱海城市,而瘦馬有可能是土生土長的濱海人,也可能是從外省來的。」

凱麗和丹恩萃雯在話劇《鱷魚》中分別飾演巧玲和瘦馬。
「文學的想像力有多大,舞台重新構建的可能性就有多高。」在巧玲和瘦馬的人物塑造上,王可然坦言,這兩個人物都不是今天的女性,而是這麼多年歷史中被構建出來的人物。「她倆表面上看是想控制男人,實際上兩個人都想用自己的努力控制自己。」
新京報記者 劉瑋
編輯 黃嘉齡
校對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