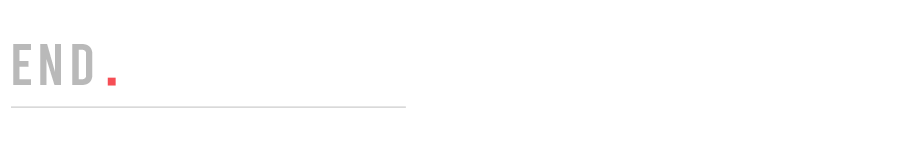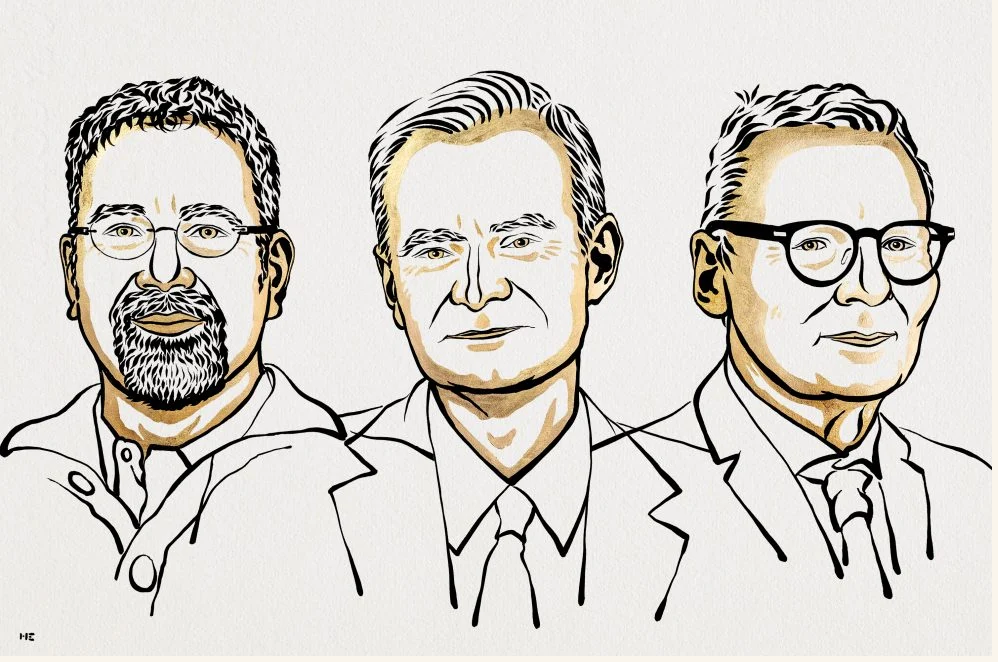為什麼越用除草劑雜草就越多?
 (來源:MIT TR)
(來源:MIT TR)七月的一個早晨,我在伊利諾伊大學南部農場的舊農學種子屋外遇見了雜草防控專家 Aaron Hager。遠處是 20 世紀初建造的圓形穀倉,旨在抵禦中西岸的風暴。當時一個數百英里寬的風暴席捲而來,伴隨每小時 80 英里的陣風,並引發了數十場龍捲風警報,讓人想起冷戰時期的炸彈演習。
農民在約 2300 萬英畝土地(約佔該州面積的三分之二)上種植玉米和大豆,以及少量小麥。Aaron Hager 在伊利諾伊州的一個農場長大,他說,他們通常會在幾乎每英畝土地上噴灑除草劑。但這些化學物質雖然可以讓一種植物在廣闊的空間里不受干擾地生長,但它們卻不再能阻止所有雜草的生長。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植物已經進化出對除草劑殺死它們的生化機制免疫的能力。這種除草劑抗性可能會導致產量下降,野蠻生長的雜草會使作物產量減少 50% 甚至更多,極端情況下可能會毀掉整塊田地。
在最壞的情況下,它甚至可能導致農民破產,這相當於農業領域的「抗生素耐藥性」,而且情況還在不斷加劇。
當我們從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的校園向東行駛時,我們看到一片大豆田,上面長滿了深綠色、尖刺的植物,長到齊胸高。
「所以問題就在這裏。那兒全是糙果莧,我猜它至少被噴灑過一次,甚至不止一次。」Aaron Hager 說,「有了這些抗除草劑的雜草,情況只會變得更糟。」
糙果莧幾乎可以侵襲任何一種農作物田地,每天生長一英吋或更多,並且該物種的雌性可以輕鬆產生數十萬粒種子。它原產於中西岸,在過去幾年中大量繁殖,因為它對七種不同類別的除草劑產生了抗性。據普渡大學推廣中心稱,來自糙果莧的季節性競爭會使大豆產量減少 44%,玉米產量減少 15%。
大多數農民仍在勉強維持生計。兩類不同的除草劑通常仍然對糙果莧有效,但對這兩種方法有抗性的物種卻越來越多。
「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失敗的到來,當然,我們還會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密蘇里大學研究雜草管理的植物科學家 Kevin Bradley 說。
而在其他地方,情況更加嚴峻。
「我們確實需要對雜草控制進行根本性的改變了,而且我們需要快速改變,因為雜草已經‘追上’了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 田納西大學植物科學教授 Larry Steckel 說。

上升趨勢
據國際抗除草劑雜草數據庫負責人、雜草防控專家 Ian Heap 稱,在 273 種雜草中,這種現像已經出現了 500 多個獨特病例,並且這一現象還在不斷增加。雜草已經進化出對 168 種不同除草劑和 31 種已知「作用模式」(化學物質旨在破壞的特定生化靶點或途徑)中的 21 種的抗性,許多除草劑都有一些共同的作用模式。
南方最邪惡的雜草之一困擾著 Larry Steckel 和他的同事,是是一種大黃紅莖的糙果莧表親,稱為長芒莧(Amaranthus palmeri),現在已發現雜草種群對九種不同類別的除草劑不起作用。這種植物每天可以生長超過兩英吋,高度可達八英呎,並「主宰」整塊田地。它原產於西南部的沙漠,擁有堅固的根系,能抵禦乾旱。如果陰雨天氣,那麼可能已經錯過了用化學方法控制它們的機會。
「長芒莧將使你種植作物的產量歸零。」Aaron Hager 說。
其他幾種雜草,包括意大利黑麥草和一種稱為「Kochia」的風滾草,正在給南部和西岸的農民帶來了真正的痛苦,特別是那些種植小麥和甜菜田的農民。

化學品誕生
二戰前,農民普遍使用犁、耙等工具進行除草、鬆土,或者他們是手工完成的。就像我母親一樣,她記得小時候在印第安納州的一個農場里鋤草。
隨著合成殺蟲劑和除草劑的出現,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農民在 20 世紀 50 年代開始使用這些殺蟲劑和除草劑。到 20 世紀 70 年代,一些最初的抵抗例子出現了。到 20 世紀 80 年代初,Ian Heap 和他的同事 Stephen Powles 發現了黑麥草種群,它們對最常用的除草劑(稱為 ACC 酶抑製劑)具有抗藥性,並在澳州南部蔓延。幾年之內,這個物種就對另一類稱為 ALS 抑制除草劑產生了抗藥性。
問題才剛剛開始,情況只會變得更糟。
20 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農業巨頭孟山都(現為拜耳作物科學的一部分)開始銷售轉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和大豆,這些作物對商業除草劑「農達」(其活性成分稱為草甘膦)具有抗性。孟山都將這些「抗農達」作物以及向整個田地噴灑草甘膦描述為控制雜草的「靈丹妙藥」。
草甘膦很快成為使用最廣泛的農用化學品之一,並且至今仍然如此。事實上,它是如此成功,以至於導致其他新除草劑的研發枯竭:似乎沒有一種主要的商業除草劑可能很快就會進入市場,從而有助於大規模解決除草劑抗性問題。
孟山都聲稱抗草甘膦雜草「極不可能」成為一個問題。當然,也有人正確地預測到這種情況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 Jonathan Gressel,他是以色列雷霍沃特魏茨曼科學研究所的名譽教授,自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一直在研究除草劑。
佐治亞大學雜草防控專家 Stanley Culpepper 於 2004 年證實了長芒莧中第一例農達抗性病例,抗性迅速蔓延。長芒莧和糙果莧都能產生雄性和雌性植物,前者產生的花粉可以在風中長距離傳播,為後者授粉。這也賦予了植物大量的遺傳多樣性,使其能夠更快地進化,更有利於除草劑抗性的發展和傳播。這些超級雜草在整個州播下了混亂的種子。
「這讓我們徹底崩潰了。」Stanley Culpepper 說道,他回憶起 2008 年至 2012 年的那段時期尤其困難,「我們一直在忙於割草。」

「活下去」
伊利諾伊大學分子雜草科學領域的領導者 Patrick Tranel 解釋說,除草劑抗性是進化的可預測結果,他的實驗室距離南部農場只有幾英里。
「當你試圖殺死某種生物時,它會做什麼?它試圖不被殺死。」Patrick Tranel 說。
雜草已經發展出令人驚訝的方式來繞過化學控制。2009 年發表在 PNAS 上的一項研究表明,長芒莧基因組中的突變使該植物能夠複製 150 多個草甘膦針對的基因複製。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雜草防控專家 Franck Dayan 表示,「這種基因擴增以前從未在植物中報導過。」
該物種產生抗藥性的另一種奇怪方式是通過稱為染色體外環狀 DNA 的結構,這是一種遺傳物質鏈,包括存在於核染色體外部的草甘膦基因靶點。這種基因可以通過風吹花粉從具有這種適應能力的植物中轉移。
但科學家們越來越多地發現雜草具有代謝抗性,植物已經進化出了分解幾乎任何外來物質(包括一系列除草劑)的機制。
假設某種除草劑對糙果莧種群起到一年的作用,如果任何植物「逃脫」或存活下來並產生種子,它們的後代可能對所用的除草劑具有代謝抗性。
有證據表明,對取代農達或與農達混合來殺死這種雜草的兩種化學物質產生了抗藥性:一種稱為草銨膦的除草劑以及兩種稱為 2,4-D 和麥草畏的物質。這兩種物質通常也會殺死許多農作物,但現在有數百萬英畝的玉米和大豆經過基因改造,因此,基本上應對措施是使用更多的化學物質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種除草劑去年有效,如果有代謝抗性,就不能保證它今年依然還有效。」Aaron Hager 指出。
位於亞利桑那州圖森市的生物多樣性中心環境健康科學主任 Nathan Donley 表示,許多除草劑會危害環境,並有可能危害人類健康。例如,百草枯是一種神經毒性化學物質,在 60 多個國家被禁止(它與帕金森氏症等疾病有關),但它在美國的使用越來越多。2,4-D 是橙劑中的活性成分之一,是一種潛在的內分泌干擾物,接觸它會導致癌症風險增加。草甘膦被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個機構列為可能的人類致癌物,並已成為數萬起價值數百億美元的訴訟的主題。阿特拉津可以在地下水中停留數年,可以縮小某些魚類、兩棲動物、爬行動物和哺乳動物的睾丸並減少精子數量。
「用 2,4-D 和麥草畏等除草劑代替草甘膦,這些除草劑通常毒性更大,這絕對是朝著錯誤方向邁出的一步。」Nathan Donley 說。

尋找解決方案
不僅僅是化學品,雜草可能會對任何類型的控制方法產生抗性。在中國的一個典型例子中,一種叫做稗草的雜草經過幾個世紀的進化,變得像水稻一樣,從而避開了人工除草。
由於雜草的進化速度相對較快,研究人員推薦了多種控制策略。Patrick Tranel 說,「混合兩種不同作用方式的除草劑有時會起作用,儘管這對環境或農民的錢包來說並不是最好的。輪作種植的作物會有所幫助,種植冬季覆蓋作物也有幫助,最重要的是,不要每年以相同的方式使用相同的除草劑。」
「從根本上講,解決方案是不要僅僅關注用於雜草管理的除草劑。這對農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也是美國農場的現狀。」愛荷華州立大學雜草科學家兼名譽教授 Micheal Owen 說。
過去幾十年來,由於農村人口外流、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化學品和轉基因作物的出現,農場規模不斷擴大,使農民能夠在大面積區域快速施用除草劑來控制雜草,這導致了作物多樣性、雜草控制實踐等方面的一種「險惡的簡化」,而雜草也已經適應了。
一方面,農民經常採取最便宜的方式來控制雜草,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愛荷華州立大學的農村社會學家 Katie Dentzman 表示,「阻礙是一個中長期問題,與短期思維和激勵體系相衝突。」
她的研究表明,農民通常對除草劑抗性知情並感到擔憂,但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這些因素阻礙了他們真正阻止除草劑抗性。一些農民表示,農場太大,如果不一次性噴灑就無法更加經濟地控制雜草;而另一些農民則缺乏勞動力、資金或時間。
Micheal Owen 認為,農業需要採用多樣化的雜草控制方法,但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的雜草防控專家 Steven Fennimore 表示,「我們的視野過於狹隘,只關注除草劑作為解決方案。」
Steven Fennimore 專注於蔬菜,除草劑的選擇很少,而有機種植者的除草劑選擇更少,所以創新是必要的。他開發了一種原型機,可以將蒸汽注入地下,殺死入口點幾英吋範圍內的雜草。這已被證明約有 90% 的有效性,他已將其用於種植生菜、胡蘿蔔和洋蔥的田地。但這種方式太慢了:處理一塊 10 英畝的土地差不多需要兩到三天的時間。
許多其他非化學控制手段在蔬菜和其他高價值作物中越來越受歡迎。最終,如果經濟和物流順利的話,這些可能會在行間作物中流行起來,這些作物可以成行種植,可以用機械耕種。
例如,一家名為 Carbon Robotics 的公司生產了一種名為「LaserWeeder」的人工智能驅動系統,顧名思義,該系統使用激光來除雜草。它的設計目的是自動在作物行中上下移動,識別不需要的植物並用 30 個激光器之一將它們「蒸發」。據該公司稱,LaserWeeders 目前在至少 17 個州開始使用。
你還可以使用電擊雜草,並且在美國和歐洲可以買到這種電擊裝置。一個典型的設計涉及使用高度可調節的銅吊杆來消滅它接觸到的雜草。這種方法最明顯的缺點是雜草通常必須比農作物要高,但是當雜草長得那麼高時,它們可能已經導致作物產量下降。
雜草種子破壞劑是另一個有前途的選擇,這些設備在澳州普遍使用,在太平洋西北地區等地也開始流行起來,在收割小麥時磨碎並殺死雜草種子。
一家名為 WeedOut 的以色列公司孵化了一種系統,可以對長芒莧植物的花粉進行輻照和消毒,然後將其釋放到田間,這樣,雌性植物就會接受到不育的花粉,無法產生可存活的種子。
「我對此感到興奮,因為這是一種減少種子庫並在無需噴灑除草劑的情況下管理這些雜草的長期方法。」Micheal Owen 說。
WeedOut 目前正在美國的玉米、大豆和甜菜田中測試其方法,並努力獲得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的批準。它最近獲得了 800 萬美元的資金來擴大規模。
密西西比大學研究除草劑的 Stephen Duke 表示,人工智能驅動的設備和精準噴灑很可能最終減少除草劑的使用。「我預計最終我們會看到機器人除草和人工智能驅動的噴霧設備接管。」但他預計大豆和玉米等作物的實現還需要一段時間,因為從經濟上來說,投入大量資金來照料如此大面積種植的此類「低價值」農作物是非常困難的。
還有少數初創公司正在研發新型除草劑,這些除草劑基於真菌中發現的天然產物或植物用來相互競爭的天然產物。但這些都不會很快投入市場。

農場日
一些最成功的預防抗藥性的工具並不完全是高科技。康奈爾大學在紐約州艾沙卡校區北部組織的「奧羅拉農場日」(Aurora Farm Field Day)上的演講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例如,康奈爾大學助理教授兼雜草防控專家 Lynn Sosnoskie 表示,為防止雜草種子傳播,農民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在收穫後清理聯合收割機,特別是如果他們從另一個州購買或使用設備。
她說,「聯合收割機已經將長芒莧引入該州,現在紐約至少已經有了五個種群。」
另一種經典方法是作物輪作,即在不同生命週期、管理實踐和生長模式的作物之間進行切換,這是有助於防止雜草習慣的一種種植方法;另一種選擇是種植冬季覆蓋作物,有助於防止雜草生長。
「我們不會僅用化學品來解決雜草問題,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開始追求一些簡單的做法。」Lynn Sosnoskie 說。
在紐約這樣的地方,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那裡的問題還沒有成為人們關注的首要問題,部分原因是該州不像中西岸那樣以單一作物為主,而且土地利用更加多樣化。
但這也不能倖免於這個問題。康奈爾大學雜草防控專家 Vipan Kumar 表示,抗性已經到來,並有可能「爆發」。
「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我的職責是教育人們,這即將到來,我們必須做好準備。」Vipan Kumar 說。
本文作者 Douglas Main 是一名記者,曾擔任《國家地理》雜誌的高級編輯和作家。
原文鏈接: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4/10/10/1105034/weeds-climate-change-genetic-engineering-superweeds-f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