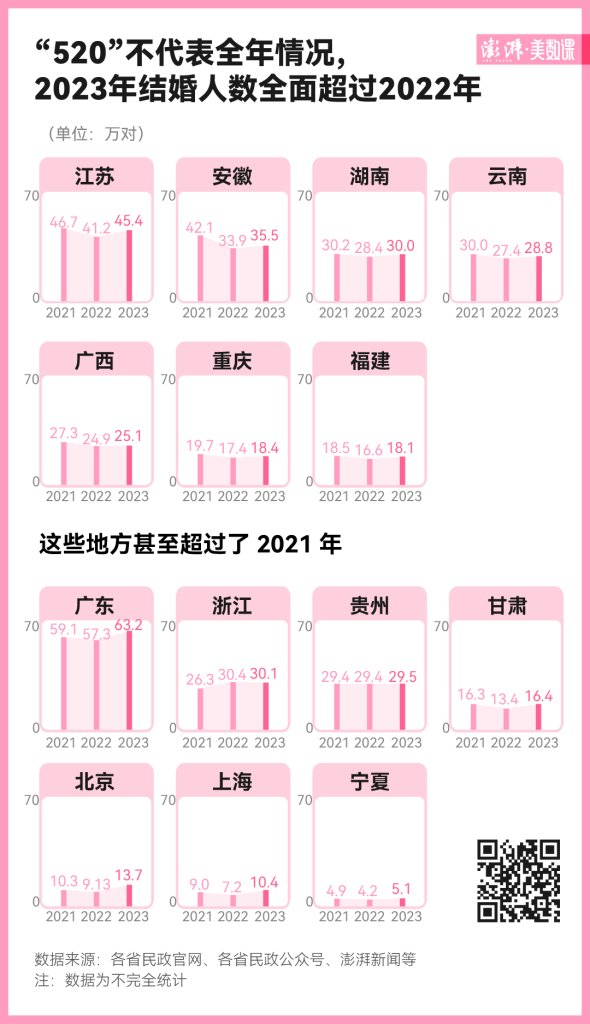是我們塑造了「潛意識」,還是「潛意識」改變了我們?

電影《盜夢空間》(Inception,2010)劇照。
下文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任性的大腦》一書。摘編有刪減,標題為摘編者所加。註釋見原書。

《任性的大腦》,[英]蓋伊·克拉克斯頓著,姚芸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1月。
「恣意」潛意識:遙遠的例子
公元前2000年,胡夫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將迎來第一千年春秋時,位於尼羅河穀中王國的古代埃及人,已經解析出相當完整的潛意識概念。他們運用本國水手熟悉的形象,創造了一個搭建著小心翼翼的道德小宇宙的神秘世界,以及一套可以提供有關死亡和夢的過程的相當高深的心理學,把內部和外部的世界都包容進來。在努恩神的世界里,你會發現神靈和魔鬼、具有象徵意義的動物和各種原型,還有後世被稱作靈魂的種種原始特徵,包括理性和潛意識,兩者快樂地(或者並非如此快樂地)相依為命。
生命的各個方面,好的、壞的和冷漠的,都會在拉神重新陷入黑暗之前,因拉神的降臨而暫時帶入理性之光。某些力量的暗示,如此黑暗而強大,它們必定從未被帶入理性之光中。這裏有費奧伊德式的早期衝突的萌芽,也有祖恩式虔誠智慧的原型。

埃及太陽神拉經歷他的夜晚新生之旅,他的太陽船行駛在阿菲波斯的腹中。這幅石灰岩壁畫發現於塞提王一世的陵墓中,大約創作於公元前1200年的新王國時期。圖片來自《任性的大腦》一書。
正是從這些生機勃勃的富有圖畫感的開端,潛意識的四千年歷史揚帆啟航。它自己的旅程豐富多彩,就好像太陽神拉所經歷的那樣,穿越其衰弱與新生、被忽略與卓越的循環。過去的二百年來,科學方式最終開始將潛意識安放在堅實的經驗土壤之中。新的進展層出不窮,不過並非全都指向費奧伊德及其門徒想要我們信服的方向,但許多事物也會被遺忘—富貴、詩歌以及可能最為寶貴的延續性。21世紀已經啟程,我們有一些關於潛意識的精選的計劃,然而卻罕有如古埃及人那樣精心設計的宏大敘事。
我們所知的潛意識,當然都是比喻和理論。我們不能把它靠牆立定拍下照片。而這些象徵性的圖像必須來自已知的世界。現代世界充滿了已有的概念和人造物,我們可以從中汲取比喻借代的靈感—水泵和數碼電腦幫助我們管中窺豹,可以比喻心與腦的動作規律。但缺少這類可知的技術形式,你必鬚根據已知事物來推斷—風景、天氣、自然節律,當然還有其他人。在缺少對他人「內在性」,包括身體構造、內在健康以及精神狀態的更多理解時,你會傾向於不再從個體的「頭腦」中為人類本性的古怪之處尋找解釋,因為那種觀念不是可以「想」出來的。你會傾向於轉向外在,到可見的形狀和行為中尋找解釋。你看著土地,你聽著雷聲,你觀察著你的朋友和你的上司,運用社會集合體的想像盡情陶造,捏合成各派勢力和角色,來支撐關於夢與死亡、瘋狂與不幸何去何從的寓言故事。

電影《潛意識分離》(Subconscious Disconnect,2012)劇照。
我們能夠大致將其來源劃分為——風景、天氣和動物的自然世界,以及權力、智慧、信任和影響力的人類世界——兩大類。
我們將看到,兩者都源遠流長。潛意識仍然會被部分地認作某個「地方」,部分被認作一套非人的力量,部分被認作潛伏人格的大集合。最初外向的事物變得抽像化,儘管潛意識的隱喻部分仍然可見。但是,讓我們首先舉例看看這些更鮮明的比喻,並探索外在事物是如何以及為什麼會內化的。為達此目的,我們必須越過時空,但在開始時,還是讓我們回到自然與土地所引發的比喻中來。
想像的來源:千奇百怪的地理特徵
特定的地理特徵和地點大方地提供著各種模擬的可能,讓我們從古埃及快速進入1500年,聆聽柏拉圖在《斐多篇》里詳盡描述的死後世界。這些描述,很明顯是根據他對火山噴發和西西里島地下河道的第一手知識寫成的。
地底下還有幾條很大很大的河,河水沒完沒了地流。河水有燙的,也有涼的。地下還有很多火,還有一條條火河,還有不少泥石流,有的泥漿稀,有的稠,像西西里噴發熔岩之前所流的那種。還有熔岩流。這種種河流,隨時流進各個空間的各處地域。
地球里有一股振盪的力量,使種種河流有漲有落地振盪……所有這些空間的地底下,都有天然鑿就的孔道,溝通著分佈地下的水道。一個個空間都是彼此通聯的(根據楊絳譯文)……相互連接的通道將大量的水由一地引向另一地,彷彿注入碗和容器中。
正如這些埃及人一樣,希臘人也有自己的地下王國之神哈得斯,他同樣神秘而擁有地界,兼具社會學與心理學意義。不必花精力確認此類形象究竟具有文學意義或是符號象徵意義,究竟是代碼或是神話,因為這類形象創造出來,不是為了像今天的人們創造全球歐元這樣一個堅挺的目標。富有多層含義使之毫無困難地同時共存並糾纏—真實的地界混合著象徵性的含義(就像現在許多原住民仍然傳唱的那樣),而神秘的人物和事件遠非幻想。所以,讀一讀柏拉圖對西西里的天然地下墓穴的描述,大多會在某種程度上聯想到繪製一種今天被稱為「模塊化思維」的了不起的預判圖畫。但是,我們必須明白,人們是以不同的標準來看待這些比喻和圖畫的,許多人也許只是滿足於文學閱讀,而其他人更留意到其中的心理迴響。希臘人當然與我們一樣,對那種突然的戲劇性的情緒爆發方式感到迷惑不解,情緒會「沸騰」,人們怒發衝冠,這時,還有什麼比用火山更能很好地打吡方呢?火山的恐怖爆發,火焰與蒸汽象徵著火與水貫穿全球以及地下潛意識世界的混亂的相互反應。

短片《潛意識之境》(2020)劇照。
柏拉圖自己展示了各層次含義是如何精密地相互交織的。在他的神秘主義世界中,有一條叫作克列拿斯河的地下河流,它的顏色是基亞諾斯(Kyanos)色的,也就是午夜藍的顏色。從詞源上講,克列拿斯河的本意就是悲傷之河;在希臘的宗教和文學中,基亞諾斯本身就是哀悼的顏色。就像埃端拿火山的不可預測一樣,怒火也會突然爆發,克列拿斯河的氾濫,也是一種不受控制的眼淚的蓄積。確實,這些不可能給予你解決大量問題的方式,讓你知道如何應對任性的情緒,但至少它們提供了一點安慰,讓你能夠將自己的情緒爆發解釋為自然現象(而不是一種個人的失敗),男神和女神們也被安排進了柏拉圖的故事里。根據神話記載,宙斯將西西里島送給珀耳塞福涅,作為她被哈得斯強姦的補償。而哈得斯擄走珀耳塞福涅的地方,叫作敘拉古的溫泉,又被稱作基亞涅(Kyane),意思是午夜溫泉,據說得墨忒耳失去女兒珀耳塞福涅所流的眼淚彙成此泉。
「地下」:潛意識的另一面
地下世界提供了創造性的自然類比,也是情緒的類比。火山是具有創造力的—新的地形輪廓來自火山熔岩的流動。大自然的力量既有建設性,又有破壞性。大地既是珍貴礦產的淵源,也是百花齊放的根源,同時也是地震與洪水的來源。所以我們發現「下凡」一詞,經年累月地使用它,把它作為利用潛意識的創造力的代名詞。
最近的例子就是19世紀的神話故事《三根羽毛》。一位老國王派三個兒子出發尋找世界上最好的地毯,以便決定誰能繼承領土。從城堡高處飄落的三根羽毛決定了他們三人前進的方向,一根往西,一根往東,而屬於最小、最「傻」王子的第三根羽毛,卻落在了城堡旁邊的地上。他失落地坐在羽毛落下的地方,然而,他注意到有一個暗門通往地下。他走下去,來到一間屋子,屋裡坐著一隻巨大的癩蛤蟆,它送給他一幅最漂亮的地毯,絕對超過他那兩個哥哥找到的普通地毯。兩個哥哥原以為小弟很傻,他們根本不需費心尋找就能擊敗他。哥哥們向父親抗議,並勸說父親再增加一輪比賽……而故事繼續著,直到「傻」王子最終被授予王冠,他「以極大的智慧」統治王國「很長時間」。那位傳說中的「傻」王子,他不會過分驕傲,願意挖掘自己的精神後院,也就是他的潛意識,從而創造出超級美麗的作品。而在外圍徘徊的聰明人,遊蕩了很久,也走得很遠,卻帶不回任何原創好作品。般奴·貝特爾海姆(Bruno Bettelheim)評論說:「下到地球的黑暗中去,好比墮入下層社會……這是一個傻子開始探索其潛意識頭腦的童話……這個故事暗示著一種局限,智力如果不依賴於潛意識,並得到潛意識力量的支撐,就會遭遇這種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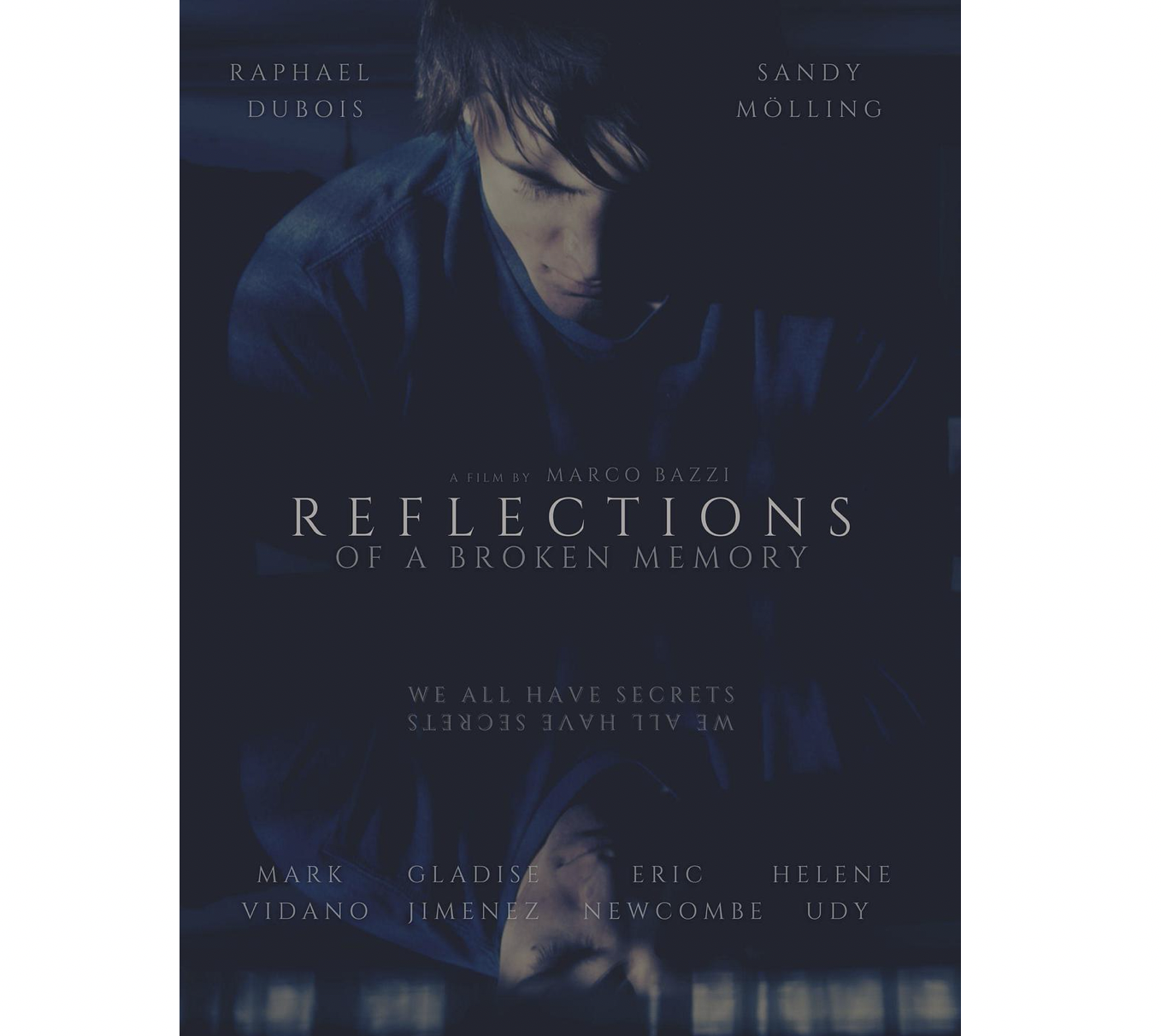 以潛意識為題材的電影海報,《潛意識罪惡》(Reflections of a Broken Memory,2022)。
以潛意識為題材的電影海報,《潛意識罪惡》(Reflections of a Broken Memory,2022)。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潛意識有其更罪惡、更致命的一面,直到今天,也是地下世界的一種象徵。喜劇和卡通經常使用這種手法。你總會在地牢里找到龍。H.G.威爾斯的經典故事《時光機》,你如果記得,愛洛伊人住在地面上,像孩子一樣歡樂又調皮;而莫洛克則害怕光,在黑暗中疾走,像騾子一樣命運勞苦,備受同情—或者時光旅行者認為開始是這樣的。威爾斯創造了這兩者之間的怪異聯繫。隨著時間的緩慢流逝,時光旅行者才帶著恐懼之心意識到,力量真正所在的地方以及真正掌握控制權的人。(《時光機》最早發表於1895年,同一年費奧伊德正在撰寫《科學心理學計劃》,費奧伊德和威爾斯都被人性的悲憫所打動,所謂世紀末憂鬱,毫無疑問,威爾斯的構思應該被歸入「心理-神秘主義」而不是「科幻小說」。)
「加工」自然風物
自然的許多其他方面,都可被加工為富有象徵意義的比喻。風、雷、磁性等可接觸的力量,構成更超凡脫俗的故事的原型,比如「上帝之怒」,或者甚至可能是風水之類看不見的能量。超凡的神靈就是這樣幻化而來,並且被認為是創造力、瘋狂、神奇的吸引力或是莫名其妙的不幸的來源。從《伊索寓言》《女巫的黑貓》到《列馬斯大叔》《格連兄弟》,帶著他們智慧的蟾蜍和狂野的侏儒,各個年代的作者不遺餘力地描述那些帶著人類的特徵、帶著或好或壞的企圖的動物,並利用它們來獲取一種虛假的實證把柄,證明根本無法解釋的事物,或者達到某種道德企圖。就像杜立特博士那樣,西伯利亞薩滿巫師會與動物對話,或者甚至將他們自己變成鳥或狗,通過這樣的手段來獲得通往超正常世界的神秘知識的明確的通道。

電影《格連兄弟》(The Brothers Grimm,2005)劇照。
在許多這樣基於自然的類比中,「往下」——下到地底,下到進化的階梯下——是一種對人類遭遇怪異體驗時的主流比喻。「黑暗」是另一處你看到的地方,潛意識的外化和內化的版本都會多多少少地使用這些指代詞語。地下世界不僅僅是一個土層下面的用於懲罰和埋葬的地方。儘管這是拉神夜間遊曆的地方,這也是一個太陽永遠照不到的地方,或者用市井的表達,就是「永無天日」的地方。黑暗是令人恐懼的—這是夜行動物擁有優勢的地方,是古魯姆發出嘶嘶聲和狼群嚎叫的地方。這是邀請我們自己潛意識恐懼的放大登場的王國。所有的貓在黑夜裡都是灰色的,但它們也可能是野人。亞里士杜特觀察說:「在有些年青人中間,即使他們的眼睛瞪得很大,眼珠也是黑亮的,但太多移動的形狀出現,以至於他們只願意將頭包裹在恐懼中。」黑暗是鬼魂出現的地方,夜晚則是燭光幽然閃爍將鬼影投射到遠處牆角的時間。
從遠古到迄今一百年前,我們的先人所知道的被黑暗吞噬的世界,要比我們所認知的更為真實,也更為常見。他們因而將黑暗想像成恐怖的幽靈,賦予各種象徵意義都情有可原。

電影《盜夢空間》(Inception,2010)劇照。
無論成人還是兒童,黑暗是所有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把黑暗看作一種形象,人們實際上是在將生命中那種潛意識的概念,那種我們無力「看穿」卻頑固而持久地存在著的神秘現象,一一地織入故事的解釋性環節里。只有在發明電燈之後,黑暗本身才成為一種純粹的陌生人,或者至少退而成為一種選項。能夠隨時打開電燈開關的人,相比於那些需要摸黑穿越房間才能碰到床邊的人,前者永遠不會體會到真正的黑暗。我們用燈光照亮了夜空,直到閉上眼睛睡覺的時候才會關上床頭燈,這樣做的後果,使我們對那薄暮冥冥、夜色闌珊激發古人想像的狀態逐漸感到陌生;對古人與鬼魂擦肩而過的經歷、古典大師筆下難以言傳的美,逐漸產生隔閡。
瓦爾特·德拉美爾(Walterdela Mare)在一篇介紹《注視夢想家》的散文中說,他的詩集是在謳歌潛意識,提醒我們:「使用蠟燭,即使只是幾個小時,也會意識到,燭光再弱,對於安靜的心靈和安靜的談話,都是多麼好的慰藉啊,更別提燭光映著安靜的臉和沉思的眼,那是何等的美麗!在黃昏時分,我們的想像更加紛擾、更加警覺、更加蓄勢待發,我們的理性頭腦如畫刷一般,此時會更親密地依偎著自己一手編織的潛意識之襯墊,越發肆無忌憚地潑墨揮灑。
原文作者/[英]蓋伊·克拉克斯頓
摘編/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