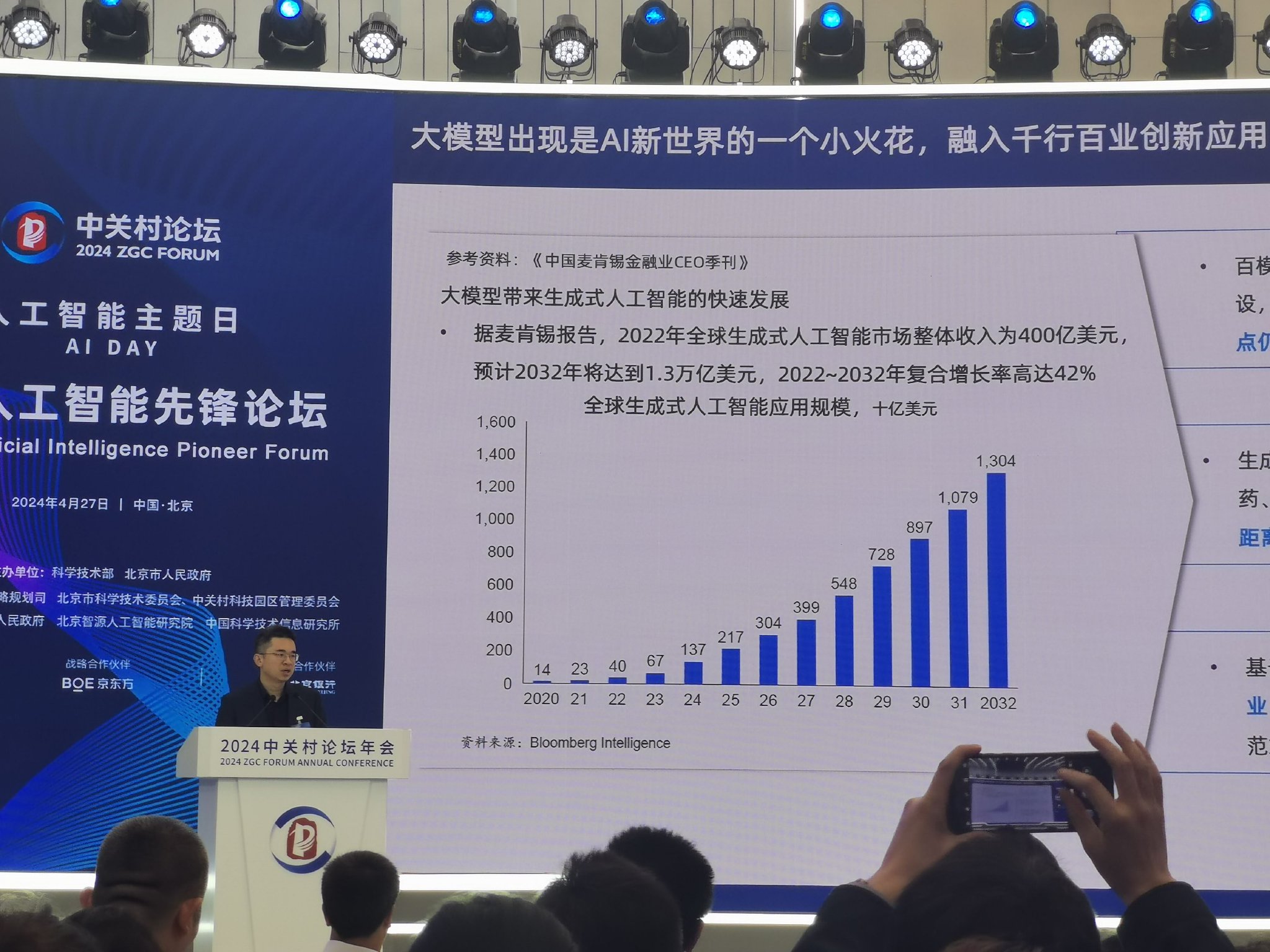劉亮程:當我積蓄夠人世的苦,就去做山窪里的黃連

《大地上的家鄉》,作者:劉亮程,版本:譯林出版社 2024年3月
「那該是活成一座山的我」
在金佛山景區入口處,他們指著對面一道山脊說,那是佛頭,那是佛身。我看了看,只是山,並沒有他們所說的佛。可能我佛緣淺,不能看什麼都是佛。也可能眼前的山並沒造化出我想像的佛相來。
其實我是不屑看那些像佛的山的。人心中有佛,佛一定生著人心的樣子。那些有鼻子有眼的山形,只是像人而已。山若成佛,也未必躺成人的模樣,它或立或臥,或高聳雲天或逶迤千里,都再自然不過。一座像人的山卻不自然了。
但我卻在金佛山看見一座像我的山。
我們沿密林中的木棧道前行,金佛山似有無盡的生長力,草木長得茂盛擁擠,讓人感覺透不過氣來,卻個個活得翠綠旺勢。行到山頂風口處,眼前豁然開朗,剛才被樹木遮擋的雲海顯露出來。風颳得正緊。是西風。我們一行人背對風,站在懸崖邊上,衣服被吹得飄起來。眼前的雲也正被風掀動。從這個山口吹去的每一陣風,都造出不一般的茫茫雲景來。
一座鐵黑色的山峰聳在無邊雲海中。雲把其它的山都抹去了,這座孤峰露出頭來。我知道在它四周,看不見的群山正積聚在雲層下方。從我們剛才經過的山穀,能看見那些雲層下的山,它們勾肩搭背連為一體。山與山之間有一條萬物生長的路,讓草色和花色延綿不絕,也讓村舍阡陌相連。更高的山峰聳入雲中,像是要把天頂破。我們登到山頂才知道,那些看上去高聳入雲的山峰,都淹沒在雲中找不見了。只有這一座山峰,探身到雲外。它穿透了天地間的無限空虛,已在雲上端坐了。
陪同者說,那是金龜山。
此時雲霧正隨風翻騰,山峰時隱時現,我並沒看出山的龜形來,倒是看見那峰頂酷似一個人的闊大額頭,連鼻子和嘴都清晰可見。我拿手機拍了兩張,拍好後看照片,竟覺得那瞬間抓拍的山形有點像我。趕緊讓同伴給我拍張合照,只片刻工夫,那人形已經不在,雲霧很快地修改了山峰,沒被雲遮住的部分,已經不再像一個人的額頭。它確實像一塊龜背,龜頭朝北向下,像是要一躍跳下去。
山與霧,在萬千變化的瞬間,霧遮去多餘的部分,露出一個人的相貌來,開闊的額頭,高聳的鼻子,黑鐵的神情。
其實我在看見它的瞬間便心中一怔,那不是我嗎?那一瞬我似乎去了山那裡,早已成為一塊石頭,被幻化的霧再現於另一個時空。它坐南面北,頭朝後傾斜,像是靠在什麼地方,但後面全是霧,它靠著空空白霧,或許只有空可以讓它的頭靠過去,只有虛空,盛得下那顆頭顱。
離開龜背石,我們沿懸空的棧道去了趟雲霧深處,棧道在雲層之上,頭頂既是山頂,行走其上,半個身體在浮雲裡,輕輕飄飄,另半個身體緊依山壁,不敢絲毫脫開和山壁的聯繫。金佛山棧道長十幾公里,一步一景,沿著峭壁可以繞過整座山。我們沒有走完全程,回返時帶隊的女士不斷朝後喊,都回來了吧。後面只有回音。人之間全是霧。說出的話也霧濛濛的。我們都疑惑地回望,棧道淹沒在雲中,剛剛穿雲走去的一行人,又穿雲回來。總覺得有一個人沒有回來。又覺得那沒有回來的人像是自己。
再次經過寫有龜背石的地方,再朝浮雲中的龜背石望,雲霧還在不住地升騰翻滾,那山峰也不斷地隨霧造型。但剛剛過去的那一瞬不會再現。我在這裏觀看一天,或一年,龜背石都不會再幻化出一個像我的人形來。那個瞬間的我已經永遠消失了。剩下的時間里,山還是山,露出雲海的山脊還是像龜背,它俯身朝下,在往深淵里馱載深淵。
回來後反復看那張照片,那座雲霧中的山,越加地像我了。
那該是活成一座山的我。
我在人群中每一次的仰頭,每一回的挺直胸脯,每一刻的孤傲清高,我都活成了我的山峰。它陡峭,奇崛,獨對雲天。
我把這樣的我藏在深山。
更多時候我匍匐在地,為草木低頭,對塵埃俯首,向陪伴自己到老的歲月彎腰。
一個活成人形的我,已經平常得連衰老都跟別人一模一樣了。
但我仍然會看山。每一回抬眼看山時,我的脊背都像山一樣挺起來。
「一定還有活成一棵樹形的我」
一定還有活成一棵樹形的我,在這山裡長了百年千年,反反復複的死去活來。某一刻我坐在樹下乘涼,並不知道我正坐在自己的陰涼里。樹在它的年輪中等來我。而我並沒有認出它。
我靠在樹幹上打盹時,我的瞌睡中有它的醒。它一棵樹一棵樹地醒過來,去年前年,更早年月的樹,都醒過來。一棵樹在時間的山野里長成自己的森林。我在人世活成無數個自己。我的每一個夢每一個瞬間的想法,都分叉成另一個我。我被自己的人群淹沒,又在其中恍惚地認出那個獨一的自己。
多少年後,我在秋風落葉中再次經過這棵樹,我不會去它身旁乘涼,天氣已經很涼了,但我的目光會被一地金黃的落葉吸引。一棵樹在山裡落盡我一世的繁華。我又在別處虛度了誰的一生。
儘管我依舊不知道,在我成為樹的時光里,一個季節已然遠去。樹和我,將再次錯過。我回去過一個人的冬天。我的寒冷不會凍壞樹的一個枝條。它在山裡過樹的漫長日子。它再不是我。我也不再是它。
但我的衰老里一定會有一棵樹的年輪。
我朝遠處的叫喊中也曾有過一棵風中大樹的連天呼嘯。它瘋狂搖動。我拚命奔跑,喊叫。
待我走不動路,我會取它的一根樹枝做枴杖。
我會躺在一棵大樹里,成為自己的木頭。我在人們不知道的春天里發芽。那時我的影子不再是黑色的,它不被看見地流淌成一條回憶之河,曲曲折折穿過生長著同一棵樹木的遼闊山野。我在那時看見自己的人群,每一刻,每一年,每一個夢中和醒來的我,聚齊在一生的荒野。
我沒說出那棵樹的名字,我想在此山中隱藏一棵樹。它不被人喚知名字。我的名字越被人所知,它便越無名。
帶我來的女子說,「這棵樹年年結小紅果,好吃極了,但我從未吃到過一顆。」
「為什麼呢?」我望著她好看的眼睛問。
「這些鳥兒,盯著樹上的每顆果子,紅熟一顆吃掉一顆,半顆都不會留給人。」
「你明年來,它會留給你一顆。」
「那你明年再來,我還陪你上山。這些鳥兒,或許真的會吃剩下一顆呢。」
「樹會多結出一顆紅果,留給你。」我替那棵樹做了許諾,但這個許諾分明又是我的。
我每時每刻說的話,都長成了它的繁茂枝葉,它的「沙沙」聲響在所有的季節里。
我每年每月的沉默,都深埋成它的根系。
而我在秋天里紅透果實等待的那個人,或許只是另一個我。
他已經來過。
「當我積蓄夠人世的苦,就去做山窪里的黃連」
還有活成一棵草藥的我吧。
金佛山被當成草藥庫,每行一步都可與一樣草藥相遇。隨行女士給我介紹沿途那些草藥的名字,許多名字熟悉卻從未見過。我小時候家裡有繁體豎排版的中醫書,先父留下的,我記住許多草藥的名字和藥性,也早早地知道了人要得的所有的病。我曾有機會去學中藥,懸壺濟世。但最終當了一個胡思亂想的寫書人。草藥的名字卻一直沒敢忘記,總覺得它們是一生中遲早要遇見的貴人,為我以後要得的一樣病而生。我一年年的終會走到一株草身旁,它是我有毒身體的解藥,我的命在它手裡。
每一株茂盛生長的草藥,都等候著世上的某個人。他出生,長大,生活,生病。老中醫給他開的方子裡,有一味藥長在金佛山的陽坡,有兩味生在金佛山的陰窪,另有一味只在絕壁上長,不肯被人采來熬煎。
那孤冷的藥草,不屑醫生老病死的俗病。
它只醫人間的清高,但清高不是病。
生老病死也不是病,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在我的書架上有民國版的《中華藥典》,有《中國中醫秘方大全》《男女科5000金方》,幾乎所有的草藥和對症的病,都寫在醫書中,我遲早要得的病也在其中。偶爾翻看,像是在找自己的病,又給病找自己的藥。那麼多千奇百怪的方子。同一種病,有完全不同的藥方,又有幾十上百種的草藥可以調劑使用。似乎只需得一樣病,便可嚐盡世間百草。
這是一劑給週歲小兒的處方:
雞內金5克/神曲5克/麥芽5克/山楂5克/薏仁5克/白朮7.5克/山藥5克/桔梗3克/茯苓5克/蒼朮5克/川樸3克/枳殼3克/乾草5克。
功能:消食導滯,健脾止瀉。主治小兒下利不爽,大便腐臭,暖吐酸腐等症。
每日一劑,每劑熬至150毫升,分4次服完。
若伴嘔吐加半夏/藿香。陣啼加砂仁/元胡。小便黃少加車前子/木通。
十幾種草藥,在一起煎熬。十幾種味道,熬到最後剩下一味苦。
都說良藥苦口。苦口,或是草藥最真實的藥用,熬給人嚐世間滋味的。
嚐過這味苦,便沒什麼不甘甜了。
那苦藥湯一遍遍地,經過孩子、大人和老人的口舌胃腸。
草藥也是陪伴。你安好時,它長在山裡,是一株草。開藥味的花,結苦籽。待到體弱多病,山裡山外的草都找來了,你不知道哪棵草對症你的病。醫生也不知道。否則他不會抓一堆草藥給你。一堆草里有一種是你的藥。但它須和其它的草熬在一起。一樣草攜帶幾十樣草,來陪伴你的病。一樣草太孤單,一味湯太苦寒。必須是十味百味雜陳。苦熬著苦,酸甜辣也熬在苦里。這樣的滋味應是人生的悲欣交集了。
一碗藥湯送走的人,帶著滿口苦味,轉世在草藥里,開苦花,結不忍給鳥兒啄食的苦澀果實,把最苦的根莖深埋。
還是被人刨出來。
女士指著坡地一棵獨稈植物說,這是鬼獨搖草。
早年我讀到過這個名字,但想像不出它的樣子。如今見到了,竟和醫書中描述的一樣:此草獨莖而葉攢其端,無風自動,故曰鬼獨搖草。
那棵草似乎聽到有人叫,微微動了下身子。它知道自己在人世有一個名字,人喚著名字到山裡找它,去治膽怯害怕的病。
鬼獨搖草學名天麻。
它就長在離我幾步遠的地方,本想采一株回去,熬湯服了。只是動了心念。我被自己的念頭嚇住。彷彿內心裡有一個跟隨多年的我不知道的懼怕,突然在一棵療治懼怕的藥草邊,顯現出來。
我小時候怕鬼,晚上睡覺都拿被子蒙著頭。後來有一天突然不怕了,開始四處找鬼。想知道那個讓自己害怕的鬼長什麼樣子。
再後來,我知道鬼活在我的念頭裡。
人的每個念頭裡都住著一個鬼。那些鬼遲早會出來。
我用一個個無鬼的念頭把有鬼的念頭壓住。或把鬼念頭帶到遠處扔掉,自己脫身回來。但那個把鬼扔掉的遠處也在自己心裡。對於念頭來說,多遠都是一念間的事。
此時一株鬼獨搖草,又讓我看見自己曾經的害怕。
或是我曾經的恐懼早已投生為一株鬼獨搖草,孤獨的稈兒,末端舉一簇花葉,搖搖欲墜,生著擔驚受怕的樣子,人卻要拿它治驚恐病。不知道它會不會被人的驚恐嚇住。
千千萬萬的草藥長在山中,我是它們中的誰呢。
在我孤苦伶仃的前世,我一定是此山裡孤傲不群的獨活,不長多餘的枝,不跟別的草合夥,生著不讓人喜歡的味,探向高處的白色花簇,只在風中自言自語。
我在今生里忘記多少人和事,才能讓那永遠不會忘記的人說一句「勿忘我」。
曾經有女子說我是她的毒藥。說完後她靜悄悄地走了。她去找時間的解藥。遺忘也是藥。回想也是。我菜地的一角種有茴香,我在什麼都想不起來的下午,摘一枝聞聞。它特別的香味里都是往事。
我會在世間所有的味道中,唯一嚐出你的香味。我會為此憂傷。
而醫治我曠世憂傷的長生草,長在金佛山雲霧纏繞的峭壁上。它在霧裡開花,霧裡結籽。我比山高的憂傷,只有看不見的遙遠星光可以療治。
但星光不是藥,它是人最需要的仰望。
就像所有的藥都醫治不了人的死亡。
死亡不是病,它是安息。
當我積蓄夠人世的苦,就去做山窪里的黃連。我嚐過黃連的葉子和根莖。在我少年時生活的河灣窪地,隱秘而孤獨地生長著一叢黃連。只有少數的人知道。更多的不知苦甜地活著的人,最苦的黃連不讓他們嚐見。
我曾因病去看過老中醫,他幹枯的手指,按在我年輕有力的手腕上。他摸過的脈大多已經平息,我的脈還在堂堂跳動。他摸出我有很長的命,有的是時光去得許多的病。他留給我一冊發黃的繁體字的手抄秘方,說我要得的病都在裡面,方子也在裡面。多少年來我一直給自己號脈,左手按住右腕,又右手按左腕。都說醫者不自醫。但我有無數個我。一個我生病時,無數個我在對面,他們長成山中草藥,長成樹,長成一座座山。
我的命在他們那裡。
2021年7月17日,木壘書院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選自《大地上的家鄉》一書,原文標題為《在金佛山遇見自己》,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劉亮程
摘編/張進
編輯/張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