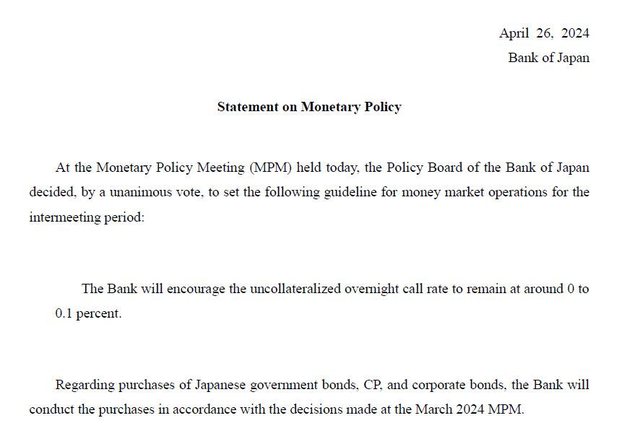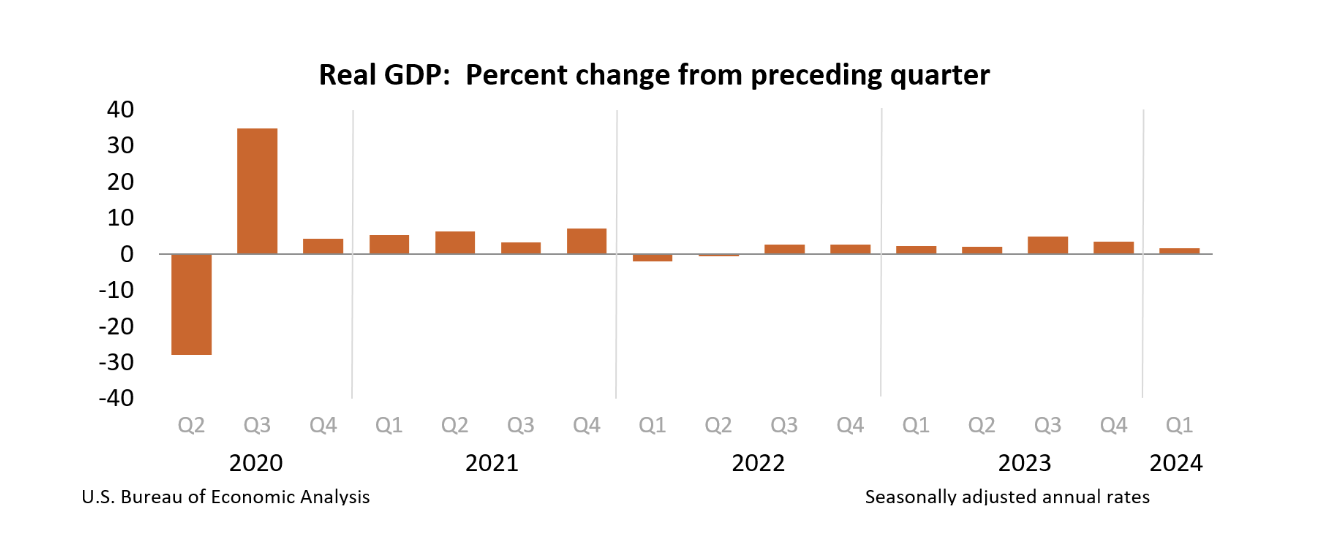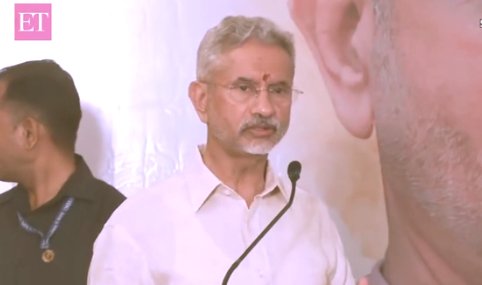巴以衝突持續,有著怎樣複雜的背景?
據新華社等消息,當地時間10月7日,多名巴勒斯坦武裝人員進入以色列境內與以軍發生衝突,同天伊斯蘭抵抗運動組織哈馬斯發表聲明將對以色列採取軍事行動。這是多年來巴以之間最大規模的衝突,目前,衝突仍在持續,雙方傷亡慘重。
衝突爆發的當天是第四次中東戰爭五十週年。自二戰結束以來,中東問題始終是籠罩在世界和平願景上的陰雲,而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衝突一直是中東衝突的代表之一。隨著19世紀末猶太複國運動的興起,曾經被迫“流散”的猶太人移居返歸巴勒斯坦地區,與巴勒斯坦人發生衝突,數十年來,雙方矛盾不斷。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首任總理本-古裡安宣佈以色列建國。次日,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在以色列著名曆史學家塞格夫看來,猶太民族複國主義的夢想與這位“以色列國父”密切關聯。古裡安的一生跌宕起伏:他曾發動巴勒斯坦本地猶太勞工壯大猶太複國主義的力量;他拒絕二戰後的分治和託管安排,“為了國家,不惜一切”,將血肉之軀送上戰場。透過這位複雜的政治人物的眼睛,我們能窺見第一次中東危機爆發的隱秘緣由,也能體會中東衝突需要付出的苦澀代價。
以下文章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為了國家,不惜一切:本-古裡安傳》,較原文有刪改。

《為了國家,不惜一切:本-古裡安傳》,[以色列]湯姆·塞格夫 著,李棟、單淩 譯,浙江人民出版,2023年7月。
“猶太複國主義者的巨大財富”
最後的戰役在加利利和內蓋夫爆發。幾年前,英國人的分治方案曾引發一場辯論,當時本-古裡安在日記中寫道,如果他必須在方案里的加利利和不在方案里的內蓋夫之間作出選擇,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加利利。1948年6月,他又說他寧願擁有內蓋夫。其實兩個他都想要。戰爭爆發時,他宣佈:“如果我們不能在沙漠里站住腳跟,我們也無法控製特拉維夫。”
本-古裡安稱這是宣佈獨立以來作出的最重要的決定。他前往內蓋夫,指導阿隆如何征服它,就像他指導雅丁征服耶路撒冷一樣。內蓋夫激發了他的想像力,部分是因為他認為這是“一片無人居住的地區”,滿足了猶太複國主義者對一個無人居住的巴勒斯坦“處女地”的夢想。
他堅持認為,內蓋夫是“猶太複國主義者的巨大財富”,它只是缺水,地下可能有石油,500萬猶太人可以在那裡定居,其中,200萬人從事農業,300萬人從事製造業。在一次內閣會議上,他滔滔不絕地談起庫爾努布,那是貝爾謝瓦東南部一座納巴泰王國城市的廢墟。整整30萬個家庭可以在那裡定居,政府辦公大樓也可以設在那裡。那兒的風景特別美。但阿隆沒有聽從他的指揮,派部隊去了西奈的阿里什,希望能占領加沙地帶。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以色列國防軍退回到以色列的領土,本-古裡安默許了。阿隆匆忙趕到特拉維夫,但也無法改變決定。為此,他永遠不會原諒本-古裡安。
當本-古裡安聽到以色列國防軍已經抵達埃拉特時,他欣喜若狂。他在日記中寫道:“如果不算獨立戰爭,這可能是過去幾個月來最重要的事。”他回憶起自己在伯爾·卡茲尼爾森的陪伴下曾兩次前往埃拉特。現在,他將開始第三次旅行,現在這是一次正式的勝利之旅——三架飛機載著一群高官和隨行人員、一名新聞官和一名廚師,飛過馬薩達。在這次訪問中,總理穿著軍裝,戴著頭巾,就像他和卡茲尼爾森一起去的時候一樣。飛機降落後,他發現自己面對著一片湖水和樹林,但那隻是海市蜃樓。
最大的戰利品歸政府所有,包括阿拉伯人的房屋和土地、農業機械、車輛和銀行賬戶里的存款——所有這些都是私人財產。戰爭的開銷使本-古裡安心事重重,有時徹夜難眠。他對內閣部長們說,缺錢是一場噩夢,讓他無法安睡。不過,他也得出這樣的結論,戰爭是有利可圖的。他說這個國家從戰爭中獲得的更多。他指的是軍工業的發展,以及英國留下的火車和軍營等,有些是無須賠償的。
當以色列國防軍攻下羅德機場時,他很激動。他寫道:“天知道以色列政府還能不能在未來10年內建成這樣的機場。”他告訴政府,機場的價值高達數百萬美元,他還說:“我現在明白了戰爭不僅僅是浪費。”但他也學會了征服者的貪婪。10年後,他回憶起當時發生的大規模掠奪,他說那是猶太人最原始的本能暴露出來了。“沒有一個群體可以倖免於此。”他說。希伯來大學的一些教職人員闖進阿拉伯知識分子廢棄的住所,拿走他們的書,存放在國家圖書館中。

電影《奧斯陸》劇照。
這個問題在內閣引發多次討論,本-古裡安表示他對此感到厭惡和震驚。“當我聽說這些行為時,我非常驚訝,”他說,“這削弱了我對勝利的信心。”他說這是“一個痛苦的意外”,他想像中的猶太人的道德觀不是這樣的。“我面對的是我從未懷疑過的道德缺陷,這是嚴重的軍事汙點,”他在另一個場合寫道,並警告道,“那些虐待非猶太人的人也會虐待猶太人。”他還說是貪婪導致了謀殺。
農業部部長齊斯林描述了一些士兵犯下的“類似納粹”的行為。為此至少設立過兩個調查委員會。本-古裡安也主動過問此事:“聽說加利利發生了可怕的事件,這是真的嗎?”1949年夏天,他寫道:“可恥的暴行:貝爾謝瓦第22營逮捕了一對阿拉伯男女。他們殺了那個男人,然後他們(22個男人)討論如何處理那個女人。他們作出決定並且照此執行了——他們給她洗了澡,剪掉她的頭髮,強姦她,最後殺了她。”他提到該營營長被判處七年監禁。
在占領的城市發生強姦事件後,本-古裡安考慮到接下來的目標是耶路撒冷和拿撒勒,便下令每一個猶太人,尤其是每一個猶太士兵,如果被抓到強姦、搶劫或褻瀆聖地,無論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都會受到“毫不留情”的槍決。他命令將拿單·奧爾特曼的一首譴責謀殺阿拉伯平民的詩發給士兵。在此之前,軍隊審查官曾阻止《達瓦爾報》發表這首詩,本-古裡安駁回了這條命令。
除了戰爭罪帶來的道德淪喪,以及他持續關注的世界輿論是否將以色列視為正義的一方,本-古裡安還有其他政治上的考量。占領埃拉特約兩週後,阿隆試圖說服他征服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中部山區,使約旦河成為以色列的東部邊界,但沒能成功。阿隆還提議應該迫使從巴勒斯坦其他地方逃到這裏的阿拉伯難民繼續向東,把他們逼到外約旦去。幾天前,本-古裡安告訴內閣,阿隆曾提議通過耳語式宣傳煽動南部阿拉伯人逃亡。本-古裡安現在把它說成是一種不可接受的策略。至此,已有成千上萬的阿拉伯人離開了他們的家園。
本-古裡安區分了那些因為害怕以色列軍隊而提前離開家園的人,以及那些留下來但被“我們的軍隊趕出去”的人。他略帶哲理地補充道:“這是可以避免的,沒必要把他們都趕走。”他同內閣分享了他對羅德和拉姆拉事件的看法。“居民收到‘不要逃亡’的明確指令,事實證明他們最後是被趕走的。”他說。他試圖與驅逐阿拉伯人的行為保持距離,給人留下大驅逐發生幾天后他才抵達羅德的印象。被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稱為悲劇的“巴勒斯坦大災難”一直困擾著他,直到他生命的盡頭。

戴維·本-古裡安,以色列政治家、第一任總理,也是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以色列國父,領導創建以色列國,1973年去世。
“你們發動了戰爭,你們輸了!”
自20世紀初以來,數千萬人被趕出他們的家園,或被殺害,或淪為難民,這些慘案大多發生在東歐國家。但是,也許是因為各大洲的人們都對聖地發生的一切特別敏感,全世界一直關注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悲劇。本-古裡安被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解釋清楚在他的領導下發生了什麼。作為一個人,一個猶太人,一個猶太複國主義者,他確信自己是道德楷模,因此他很難將驅逐阿拉伯人的行為與他宣稱的人道主義價值觀相調和。
在他成為總理後不久,有人提議他在耶路撒冷南部的塔比耶街區的一棟豪宅里建造自己的官邸。這是一座兩層樓的石頭房子,樓梯在室外,外觀莊嚴,入口處是一個形似馬蹄鐵的巨大的石拱門。有一些鬆柏樹遮蔭,院子裡還種著一棵棕櫚樹、一棵橄欖樹和一棵檸檬樹。和這個地區的許多房子一樣,它建於20世紀30年代,是黎凡特地區富裕的寫照,也反映了當地的英國和法國文化。
塔比耶的大多數居民是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精英,住在這裏的也有英國政府官員、醫生、律師和商人。在耶路撒冷,沒有比這更有名望的社區了。它的街道沒有名字,它的房子沒有編號。舉個例子,人們只需簡單地問“安尼斯·賈馬爾的房子”在哪裡。那原本是提議給本-古裡安的住宅。賈馬爾靠保險和旅遊生意發家。他的妻子是俄國貴族,演員兼作家彼得·烏斯季諾夫是她表兄。一些猶太人也住在附近。其中一位出版商魯文·馬斯(Reuven Mas)是當地猶太居民委員會的負責人。在這座世界上最國際化的城市里,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生活在一種多元文化共存的幻覺中——前提是這種幻覺還能持續下去。到了1947年底,幻覺破滅了。
1948年1月,馬斯失去了他的兒子丹尼,丹尼曾指揮一隊士兵去解救埃齊翁街區,但在途中被阿拉伯人殺害。四周後,《達瓦爾報》稱:“昨天下午,一輛哈加納的車駛過塔比耶,呼籲居民撤離該社區。許多阿拉伯人離開了。”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在英國當局的保護下回來了。當時,《達瓦爾報》記者想著:“也許我們錯了……當我們用擴音器告知阿拉伯人必須撤離塔比耶時。”但阿拉伯人很快又逃走了,大多數人幾乎留下了全部財產,從三角鋼琴、婚紗到網球拍、廚具、書籍和家庭相冊。許多阿拉伯人的房子都被猶太人占有,這些猶太人也來自精英階層,包括政治家、法官和希伯來大學的教授。
本-古裡安參觀了耶路撒冷廢棄的街區,他拒絕搬進賈馬爾的家。總理辦公室的官員什洛莫·阿拉齊(Shlomo Arazi)推薦了這處住宅,後來他回憶起本-古裡安拒絕的原因——讓以色列總理住在一個從阿拉伯人那裡沒收的私人住宅是不合適的。當時,以色列已經從阿拉伯人手中沒收了成千上萬棟的房屋,但本-古裡安想在他自己和這一切之間劃清界限。他更願意在里哈維亞建造總理官邸,那是以色列政府從英國政府一名高級官員的遺孀那裡租來的房子,這名官員在大衛王酒店爆炸事件中喪生。

電影《奧斯陸》劇照。
本-古裡安平靜地接受了阿拉伯人流離失所的事實——他估計在50萬到60萬,其他人認為這個數字是75萬。這就是猶太人在以色列地尋求獨立付出的代價,用他的話說,這是“一片被占領的土地”。“戰爭就是戰爭。”他補充道。他的同事們都支持他。有人把阿拉伯人的離開稱為一個神聖的奇蹟,也有人說沒有阿拉伯人的話,這個國家的風景要好得多。什洛莫·拉維認為:“在我看來,阿拉伯人離開這個國家是最公正、最道德、最正確的事情之一。”他說這一直是他的觀點,甚至在兩個兒子被殺之前就持有這種觀點。本-古裡安同意他的朋友伊紮克·本-茲維的看法,他對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數量感到擔憂,大約還有10萬人。“這個國家的阿拉伯人太多了”,本-古裡安這樣認為。
本-古裡安一直否認阿拉伯人是被迫逃離的。有時他還說,“沒有難民逃離以色列國,所有從聯合國分配給猶太國家的領土逃離的難民都是在英國委任統治期間逃走的。”事實上,近一半的阿拉伯人在猶太國家建立後成為難民,但本-古裡安說這些人不是難民——他們是敵人。
不過,難民的存在和他們的困境讓他無法停下來休息。鬼城和廢棄的村莊吸引著他,他一次又一次地在阿拉伯人的街道上遊蕩,彷彿要親眼證實那裡沒有阿拉伯人,也許也是為了說服自己,他沒有出手驅逐他們。“這座城市幾乎空無一人”,這是他對雅法之行的總結,10年前,他曾幻想過雅法會被摧毀。“到處都是戴著塔布殊帽的阿拉伯人。”他寫道。在拉姆拉,他四處尋找,但沒有找到1906年他和他的朋友們創作《錫安工人黨宣言》的那間房子。他抱怨道,那座建築本應得到保護。
和他參觀完海法廢棄的猶太社區後一樣,他強調無法理解阿拉伯人為什麼要逃走。他說,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事件”。重要的是,他要指出,與猶太人不同,阿拉伯人“輕而易舉”地放棄了整座城市,即使沒有毀滅或屠殺的危險。雅法甚至不存在糧食短缺。
“很可能他們在逃跑時得到了一些幫助,”他說,“但從根本上說,這確實是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他們沒有被趕出雅法。他們甚至在雅法被攻占之前就逃走了。他們逃離了海法,逃離了太巴列,逃離了采法特。這件事很奇怪,值得研究。”
他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他認為阿拉伯人的逃亡表明阿拉伯人的民族運動無論是在文化、經濟還是社會層面,都不是基於積極的思想,他們擁有的只是宗教仇恨、仇外心理和統治者的野心。他說,一個國家不能為這樣的觀念而戰,因為沒有哪個農夫願意為這些而犧牲自己。“曆史已經證明,”他強調,“誰才是真正與這片土地相連的人,對有的人來說,這片土地不過是一種奢侈品,可以很輕鬆地拋棄它。”

電影《奧斯陸》劇照。
這是一個討好猶太人的觀點,但並不準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想阻止以色列國的建立,但無論在組織還是領導方面都沒做好準備。他們還沒有從10年前英國對阿拉伯人起義的鎮壓中恢復過來。在英國統治巴勒斯坦的最後幾個月裡,英國人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阿拉伯人逃亡。在英國委任統治巴勒斯坦的30年里,阿拉伯人沒有義務教育制度,每10個阿拉伯兒童里,只有3個上過學,其他人是在對現代國民生活毫無準備的情況下長大的,尤其是在農村,也包括海法、雅法和其他城市的邊遠地區。
相比之下,幾乎每一個猶太兒童都上學,大多數成年人在自己的原籍國上學。伊紮克·本-茲維曾引用一位阿拉伯友人的話說,巴勒斯坦衝突是100萬阿拉伯農夫和100萬愛因斯坦之間的對抗。儘管如此,仍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被迫離開家園。
耶路撒冷市長丹尼爾·奧斯特(Daniel Auster)向本-古裡安報告,一場名為“大逃亡的精神疾病”已經影響了這座城市里的猶太人。本-古裡安下令不允許猶太人離開這座城市——他們本該用自己的身體保衛這座城市。他還拒絕了撤離兒童的建議。就像一戰期間猶太人從巴勒斯坦撤離一樣,本-古裡安延續了他在1938年從納粹手中和集中營里解救兒童的做法,他認為撤離耶路撒冷的兒童就等於在向敵人投降,因此不允許這樣做。他還說,巴勒斯坦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接納兒童。
據本-古裡安所說,一些住在米亞謝阿里姆的哈瑞迪人已經舉白旗投降了,還有一些猶太人被趕出了自己在特拉維夫和一些廢棄定居點的家。這些定居點曾是猶太複國主義的象徵,比如馬薩達和沙阿戈蘭,這兩個基布茲農場都在加利利的南面,那裡的居民也不想犧牲。本-古裡安說他不知道如果他處在這些人的位置會有什麼反應。南部尼紮尼姆(Nitzanim)基布茲的居民被埃及人俘虜了。
到戰爭結束時,大約有6萬猶太人成為難民,被迫離開社區、城市、基布茲和其他農業社區。“如果穆夫提占領了耶路撒冷老城,他就會屠殺所有的猶太人。”本-古裡安說,如果穆夫提到達特拉維夫,他也會這麼做。後來,本-古裡安堅持猶太人要求阿拉伯人留下來的說法,認為他們逃亡是因為穆夫提的命令。在這一點上,他和過去一樣,強調猶太複國主義者應該感謝穆夫提犯下的所有錯誤。
本-古裡安希望阿拉伯難民會被鄰國吸收,這樣難民問題就會自動消失。“一切都會平靜下來,煙消雲散。”他說。外交部把這種幻想變成了一種不切實際的政治預測。本-古裡安畢生致力於猶太人的主權問題,實現流散的猶太民族長期以來的夢想,卻沒有意識到流亡中的團結力量和對巴勒斯坦家園的渴望。
他的內閣成員中至少齊斯林提醒過他這一點。“成千上萬的阿拉伯人,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將成為我們的敵人。正如我們從苦難中吸取教訓,明白戰爭的必要性一樣,他們也會產生報復、賠償和回家的渴望。”不過,本-古裡安認為,時間對以色列人更有利。他堅持認為,會有100萬猶太人取代阿拉伯人。
有時,他會提出討論難民返回的可能性,包括拉姆拉和羅德的難民,但這主要是為了提高以色列的國際形象而擺出的外交姿態。以色列當時還沒有被聯合國接受。本-古裡安說:“南非不需要同情、幫助和金錢,所以它可以對世界指手畫腳。我們的立場不一樣。”這也是為什麼他在最後一刻否決當地指揮官的命令,拒絕驅逐拿撒勒的阿拉伯人。
當時離立憲選舉還有兩週,他還在等待以色列向美國貸款1億美元的請求獲得批準。成千上萬的難民試圖越過邊界,回到家園。戰後以色列明確阻止難民返回,驅逐“潛入者”,導致他們的悲劇不斷延續。然而,本-古裡安命令只驅逐“潛入者”,而不是離開家園但仍留在以色列國境內的難民。有一次,他突然情緒爆發,用“你們”指代難民,好像他們突然出現在內閣會議室里:“你們發動了戰爭,你們輸了!”

電影《奧斯陸》劇照。
“我們的秘密武器”
列維·艾希科爾(Levi Eshkol)後來說,在本-古裡安最困難的時刻,他常常哼唱1938年流行的歌曲《正在燃燒》,這首歌講述的是一座猶太小鎮被燒燬的故事。居民們呼籲他們的猶太兄弟用鮮血來撲滅大火。他不時提到大屠殺,作為政治辯論的一部分。“我們不會像綿羊一樣被屠殺。”他在與英國高級專員的最後一次談話中說。他還說,希特勒試圖毀滅整個猶太民族的做法並非首創,他堅持認為穆斯林在這之前就已經這樣做了,他列舉了穆斯林犯下的一系列戰爭罪行,從穆罕默德到穆夫提在柏林的活動。他說他們只知道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唯一方法——徹底將其毀滅。
在這樣的時刻,他的話聽起來好像這是一場他個人對抗納粹的戰爭。他把造成數十人死亡的特拉維夫空襲行動稱為“埃及閃電戰”。在倫敦經曆閃電戰大轟炸的時候,他有時拒絕進入防空洞。他後來也這麼做,並為此感到自豪。當有人提議將他的辦公室搬到更安全的地點時,他的回應是:“我理解爆炸會引起精神緊張,不過我的經曆比你們所有人都多——我在倫敦經曆過。爆炸並沒有那麼可怕。”
儘管英國人支持的是外約旦阿拉伯軍團的阿卜杜拉國王,但本-古裡安對英國的曆史文化,以及英雄氣概的欽佩絲毫未減。他用一種懷舊的語氣向政府講述英國最輝煌的時刻,包括招募英國女性參戰。“在倫敦,從司機到售票員,沒有一輛公共汽車不是由女性駕駛的。武器工廠也是如此。”他堅持認為,戰時以色列應該用同樣的方式動員婦女。在他作為軍隊統帥遭到外界非議時,本-古裡安經常提及丘吉爾的名字,將其作為平民軍事領袖的榜樣。
本-古裡安也做過關於“熱血、汗水和眼淚”的演講,並經常使用英語詞彙“D-Day”(D-Day是常用軍事術語,指軍事攻擊開始日。最早出現在一戰期間,因行動日期未定或保密而暫用D-Day為代號。最為人熟知的D-Day,則是二戰期間1944年6月6日展開的諾曼底登陸。——編注)。當他一再強調以色列需要為第二次大屠殺做好準備時,他拔高了在他的領導下取得的勝利成果,培育了兩個深深嵌入以色列身份認同的神話:少數對多數,善對惡。
在戰爭之前、其間和之後,他經常說70萬人面對3000萬人,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比例是1:40。這既誇大了危險的程度,又提升了勝利的意義,既正確又不正確。在巴勒斯坦,人口結構發生迅速改變。阿拉伯人的流亡導致猶太人逐漸占大多數,在1948年的一整年里,超過12萬猶太移民來到巴勒斯坦。1948年底,本-古裡安指出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作戰部隊人數已經幾乎相等。“到目前為止,人們的觀點是阿拉伯人是多數,我們是少數,但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就阿拉伯居民的總數而言,這是正確的,但就與我們作戰的軍隊而言,這是不正確的。”雙方都派出約10萬士兵,得益於來自海外的裝備,以色列國防軍穩步發展,不斷壯大。
但這個故事的以色列版本是一個以色列的大衛和一個阿拉伯的歌利亞之間的戰鬥,比數字聽起來更有說服力。在個別戰役中,這是正確的。獨立戰爭後的許多年里,本-古裡安繼續宣傳這個神話。他從曆史的角度講述了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正是由於希伯來勞工的勝利,一個猶太國家才得以建立。”在回覆一封關於這個問題的來信時,他將這一點重複寫了不少於六次。
他一再說以色列國防軍的力量來自以色列的道德優越感。“我們的人……比我們的鄰居……更有優勢。”他無數次強調這一點。他相信以色列國防軍在道德上是卓越的,這樣的信念根植於他多年來的民族自我優越感。“阿拉伯人不像我們歐洲人那樣複雜。”他曾評論道。戰後,他宣佈:“除了土耳其,這些國家沒有能力與我們一戰。”
他有時會引用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對生命態度的不同:“對我們的對手來說,損失的數目並不重要——他們有數百萬人。”有時,他會讚揚阿拉伯人的戰鬥方式,即便如此,也是為了放大以色列國防軍的勝利。有時他誇口說:“直到現在,我還認為我們的秘密武器是我們的精神,這的確是真的。”他說:“但我們更秘密的武器是阿拉伯人,對他們的笨拙,我無法用語言來形容。”

電影《奧斯陸》劇照。
但他也可以為以色列的勝利給出更為世俗的理由,最具體的就是武器購買,以及以色列從美國猶太人那裡得到的援助,包括士兵、軍事專家和資金。他曾簡單地說過:“我們勝利的原因是阿拉伯人特別弱。”
戰爭於1949年3月結束,持續了16個月。阿拉伯國家沒能征服以色列,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雙方簽署了停戰協議,建立了臨時邊界——所謂的綠線。它或多或少與本-古裡安在三年前(原文為七年前,但前文提到本-古裡安在地圖上畫出分界線是在1946年,據此推算則為三年前,故進行了更正。——編注),用手指在貝文擺出來的地圖上劃出的分界線相吻合。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和外約旦瓜分。
以色列的領土比聯合國分治決議中給予猶太國家的領土要大,新增的土地為以色列提供了原計劃里沒有的領土連續性。阿拉伯人作為一個少數群體留在了以色列,這與本-古裡安1937年以來所說的目標一致,這些都是戰爭的主要成就。“除了為死去的兒子們感到悲傷,我們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他說。
戰爭結束前幾週,本-古裡安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和平至關重要,但不能不惜一切代價。”在獨立前的幾年中,人們曾經提出無數處理巴勒斯坦問題的方法——夥伴、聯邦、分治、自治、州、委任統治和託管,幾乎窮盡了所有可以想到的方法。一些解決方案為在歐洲難民營里的猶太人提供了定居巴勒斯坦的機會。
但是,任何一種避免戰爭的安排都不能滿足猶太複國主義的基本要求,即在猶太人占多數的前提下獨立。本-古裡安本人一直堅持認為,戰爭也許是不可避免的。“(我)預見到了戰爭的必要性。”他說。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國家生命曆程里的曆史性時刻,一個絕不會再發生的特殊時刻。這需要一個勇敢的決定,一個暴力而殘酷的決定,來實現一個新的開始,向更美好的時代過渡。在這個階段,沒有理由相信阿拉伯人會心甘情願地與巴勒斯坦的猶太國家達成協議,因此有必要通過武力使這個國家成為現實。
當本-古裡安帶領他的那一代人走進戰爭時,他是在深思熟慮後冒了一定的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分治的邊界,當然也付出了必要的代價。代價是沉重的——將近6000名以色列人死亡,幾乎每100人中就有1人死亡,包括2000名平民。每3名死者中就有1名是在耶路撒冷或內蓋夫被殺害。還有1.2萬人受傷。
以色列方面的高傷亡率很可能是由於本-古裡安未能更早地組建正規軍隊,以及他堅持由自己來指揮這場戰爭。勝利的榮耀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儘管他在戰前對安全事務處理不當,在戰爭過程中作為總指揮暴露出種種缺陷,當然也有例外,他為以色列建立了軍事工業,從海外獲得了大量武器。他渾身洋溢著軍人般的樂觀情緒。
“有一天,一個年輕的截肢者跑來找我,”他告訴內閣,“他們給他做了一個臨時義肢,他感覺很棒。我陶醉於眼前的這一幕。”他談到和一家製造假肢的英國工廠的合作,並計劃在以色列建立類似的工廠。他承諾“我們將有一個優秀的工廠”,一年半後這家工廠開業了。這是一段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沒有人知道以色列如何與鄰國達成永久的協議。“阿拉伯人不相信我們,我能理解。”果爾達·梅厄說。本-古裡安回應道:“甚至有更多的猶太人不相信我們。”這樣的說法並不準確,但能折射出他被一種失望的情緒所折磨,這不是他希望建立和領導的國家。
原文作者/[以色列]湯姆·塞格夫
摘編/劉亞光
編輯/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