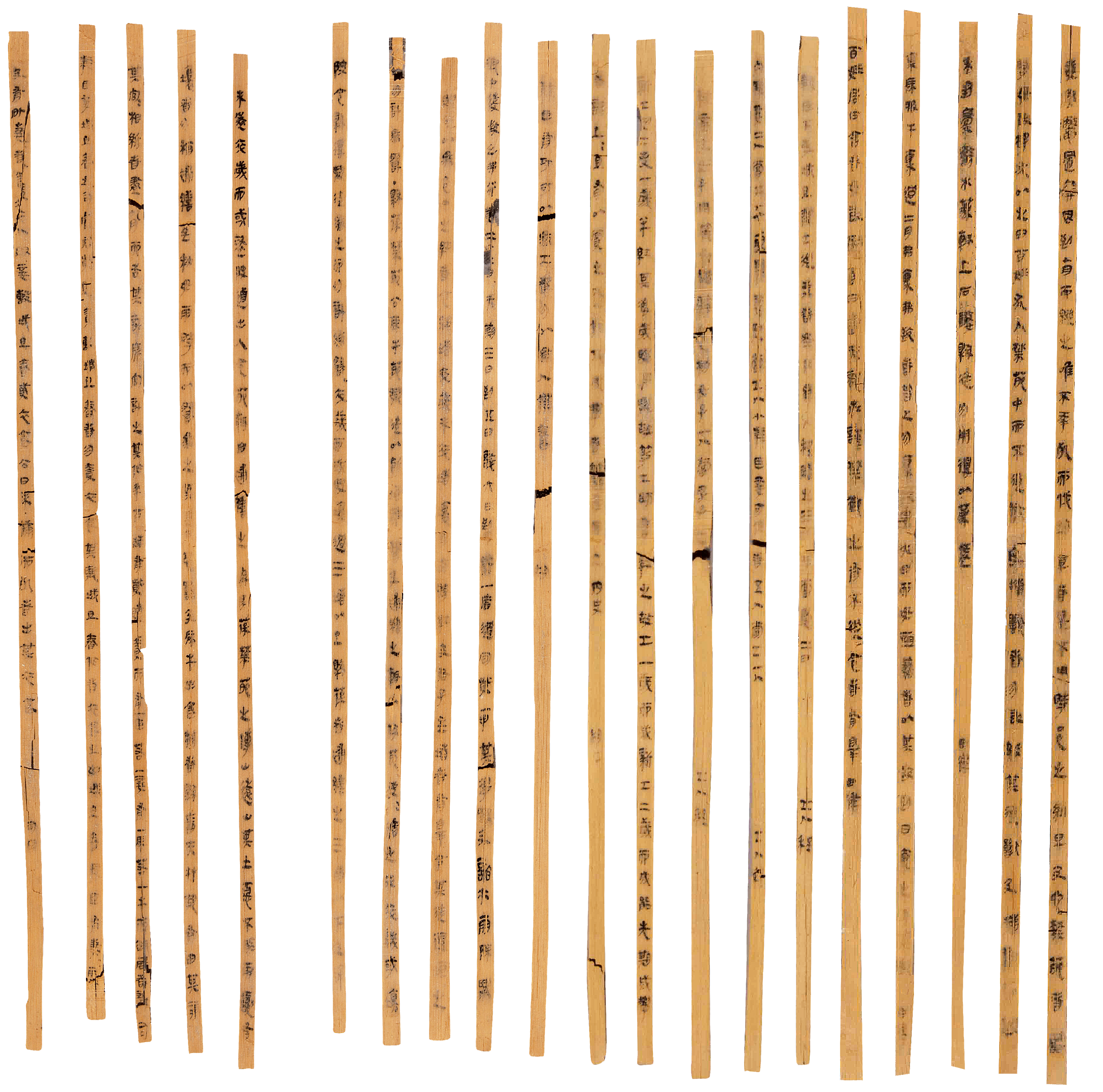《2:22》中文版導演張慧:只談懸疑驚悚,會委屈劇本和創作
2021年8月,一部名為《2:22 A GHOST STORY》(以下簡稱《2:22》)的舞台劇在倫敦西岸的奴爾·考禾特劇院首演。在這部作品正式亮相前,人們更多的是關注該劇首輪演出的女主角——英國流行女歌手莉莉·艾倫,是否能勝任她的西岸舞台首次亮相。在首演夜之後,《2:22》表現出極強的市場水平,次年在英國兩項重要頒獎禮WhatsOnStage與羅倫斯·奧利弗獎上獲得多項大獎與提名,其受歡迎程度甚至讓該劇編劇丹尼·羅達雷爾-萊特(Dorell Wright)都大感意外。
2022年上半年,大麥「當然有戲」便關注到這部作品。該劇聯合製作人崔顥回憶,第一次讀劇本的時候,便覺得《2:22》是一部兼具藝術性與商業性的優質舞台作品,雖然其自身所具備的懸疑驚悚的元素是吸引很多觀眾走進劇場的原因,但若大家沉下心來看完這部作品之後,會發現作為一部「英倫客廳戲」,它是通過不同人物角色之間密集的對話在推進劇情的發展,無論從敘事結構與情感表達都非常打動人。崔顥表示,「正如編劇丹尼·羅達雷爾-萊特(Dorell Wright)筆下創造的角色‘Sam’一樣,從《2:22》能看到他淵博的學識,涉及物理學、心理學、歷史文化、藝術影視等諸多方面。在此次的中文版製作中,張慧導演儘可能保留了他原汁原味的英倫氣息,加上編劇在劇中埋藏的諸多知識點與需要觀眾自己去發掘的舞台細節,會讓人產生一刷再刷的觀劇慾望。」

《2:22》中文版劇照。
此次,《2:22》中文版製作,大麥「當然有戲」繼續邀請已經連續合作了《雜拌、折羅或沙拉》《單寧》兩部舞台作品,在年輕戲劇觀眾中收穫口碑無數的優秀青年編劇、導演張慧執導,而該劇也將於4月19日-21日登台北京保利劇院。《2:22》中文版首演前,新京報對話導演張慧,聽她講述創作背後的故事。
一部經得起推敲的現實主義戲劇
新京報:在尚未看到這部作品的舞台呈現之前,《2:22》最為人所稱道的便是丹尼·羅達雷爾-萊特(Dorell Wright)的劇本創作,你最初看到這個劇本的感受如何?
張慧:第一感受就是成熟,不僅是一部經得起推敲的現實主義戲劇,又兼具商業性。在讀劇本的過程中,完全被他所營造的氣氛,以及環環相扣的情節發展所吸引,每一個情節的推進,你都能感受到一次懸念的轉移,感覺非常好。後來在排演的過程中,我們又發現了越來越多的新東西,看著這些人物關係一點點被建立起來的過程非常讓人愉悅。
新京報:對比同類懸疑驚悚題材的作品,你覺得《2:22》的過人之處在哪裡?
張慧:比同類題材更加現實。與我們通常看到的一些「鬼故事」,為了營造某種可怕的氛圍,將故事情節與人物狀態表現得非常片面化。而在《2:22》這部作品中,每個人物對於「鬧鬼」這件事的反應都很真實,他們都在自己的規定情境里表達著各自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沒有讓作品因懸疑驚悚而變得故弄玄虛。一切劇情都在自然地發生,從中也可以窺見編劇對於人與世界之間某種關係的理解。

在《2:22》中,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規定情境里表達著各自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新京報:《2:22》的人物角色設定和敘事手法上,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張慧:首先是劇中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女主角珍妮作為一名新手媽媽,一直以來,她都很聽從於身為物理學家「Sam」的話,直到「有鬼」這件事的出現,她突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難道真的僅僅是因為這件事的發生嗎?其實不是,或許因為她有了孩子以後,對自己的人生有了全新的梳理與感受,而「有鬼」這件事情只是一次爆發點。
另外,編劇還在角色之間設定了幾個對立點,例如,階級的對立,知識分子與普通工人的關係;蜥蜴腦與猴子腦的對抗,這源自美國神經科學家保羅·馬克萊恩提出的「三重腦」理論,他認為,猴子腦代表新哺乳動物腦,負責「理智和語言」;蜥蜴腦指爬蟲腦復合區,代表著「本能」;老鼠腦指舊哺乳動物腦,控制「慾望」。在這部劇中,大部分都在說「蜥蜴腦與猴子腦的對抗」,但我覺得,沒有提到的老鼠腦更重要,老鼠腦作為人情感中的慾望,一直在推波助瀾,像一股暗流承受著很多東西。
編劇作為一名喜劇演員,其實在劇中這些人物的對話當中,設下了一些耐人尋味的幽默,會讓觀眾在某些劇情發展中,保持著會心一笑的狀態,因此《2:22》除了其自帶的懸疑驚悚屬性之外,也是一部兼具驚悚與生活潛流的喜劇。

編劇在劇中人物的對話中設下了一些耐人尋味的幽默。
新京報:《2:22》跟你之前導演過的題材有什麼不同?
張慧:這是一部依靠人物間的對話推進整個劇情發展的作品。在我看來,這部劇討論的命題非常傳統,即「人類何去何從」這類的話題,包括我們剛才提到的蜥蜴腦與猴子腦的對抗,而沒有提到的老鼠腦才是慾望與情感最主要的動力,最終承受併發泄出的結果。這部作品最可貴之處在於,編劇沒有在某些觀點強上「價值」,我覺得觀眾不管持他們之中的哪種觀點,或更像劇中的哪一個人,他們都能在《2:22》里找到各自對應角度與立足點。
不刻意營造「驚悚」感,觀眾二刷會有更多新發現
新京報:懸疑驚悚與現實主義這兩種概念並存在同一部作品里,讓人不得不想到「唯心」與「唯物」兩種並立的主義,作為導演如何平衡二者在劇中的表現關係?
張慧:首先,我覺得唯物主義是我們人類認知世界的一種工具與方法,如果一切都是不可知,或者一切都是無法把控和解釋,我們人類便無法真正地去認知世界。在這部作品中,探討的問題很多,並不限於在所謂唯物、唯心之間的討論,還包括了我們之前提到的階級對抗,性別對抗,婚姻當中親密關係,也談到女性團結等諸多話題。
我覺得劇本寫得好的原因,在於編劇沒有片面地講述「有鬼」這件事,而是通過劇中人的聊天、辯論把各自對於「鬼」這件事的態度表達出來。據我所查,這是他寫的唯一一部話劇,他自己在BBC做了一檔就是關於靈異探索的節目,他一直認為整個世界對於「有鬼」這件事,以及所謂見到「鬼」的這些人是極度不公平的,多數觀點認為,這些人一定是因為壓力過大,或者精神出現問題,所以在這部劇的四個人物中,其中一個人物是心理醫生的,我覺得也是編劇的一個特別用意。

編劇通過劇中人的聊天、辯論把各自的態度表達出來。
新京報:對於「英倫客廳戲」,其實很多年前你就排過哈囉德·品特的《背叛》,對於排演這類形式的戲劇比較有挑戰的地方是什麼?
張慧:這類戲劇雖然人物關係並不複雜,但台詞量巨大,非常考驗演員的表演。我們在排練過程當中,在儘量保持原汁原味英倫氣息的前提下,要不斷地去挖掘演員們在此時此刻規定情形中,保持每句台詞最真實地表達與最準確的表演狀態。與此同時,演員每演一次給到彼此的內容,也在發生著變化。在大的情境裡面,每一次小的情境中微弱的變化,演員還要馬上真實地反映到自己的表演之中,這些都是很難的。
新京報:懸疑驚悚題材作品的現場觀感很關鍵,作為導演你會為觀眾營造怎樣的現場感?
張慧:《2:22》確實是一部具有懸疑驚悚觀感體驗的作品,觀演過程中不乏令人不寒而慄的時刻,但也不要忘了其本身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現實主義佳作,因此在舞台表現手法上,絕不會刻意在某些情境中,沒有任何理由的故意去「嚇」觀眾,這種手法本身就會讓人感到不舒服,產生不好的觀感。

《2:22》本身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現實主義佳作。
新京報:你希望觀眾帶著怎樣的心態來進劇場看這部作品?
張慧:其實我一直覺得,如果宣傳只說這部作品是一部懸疑驚悚劇的話,可能會有點委屈這個劇本和我們的創作。我覺得當一些回憶與舞台細節交織在一起時,觀眾一定還有想看第二遍的衝動,相信當他再來看時,又會產生不一樣的感受與新發現。
新京報記者 劉臻
編輯 徐美琳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