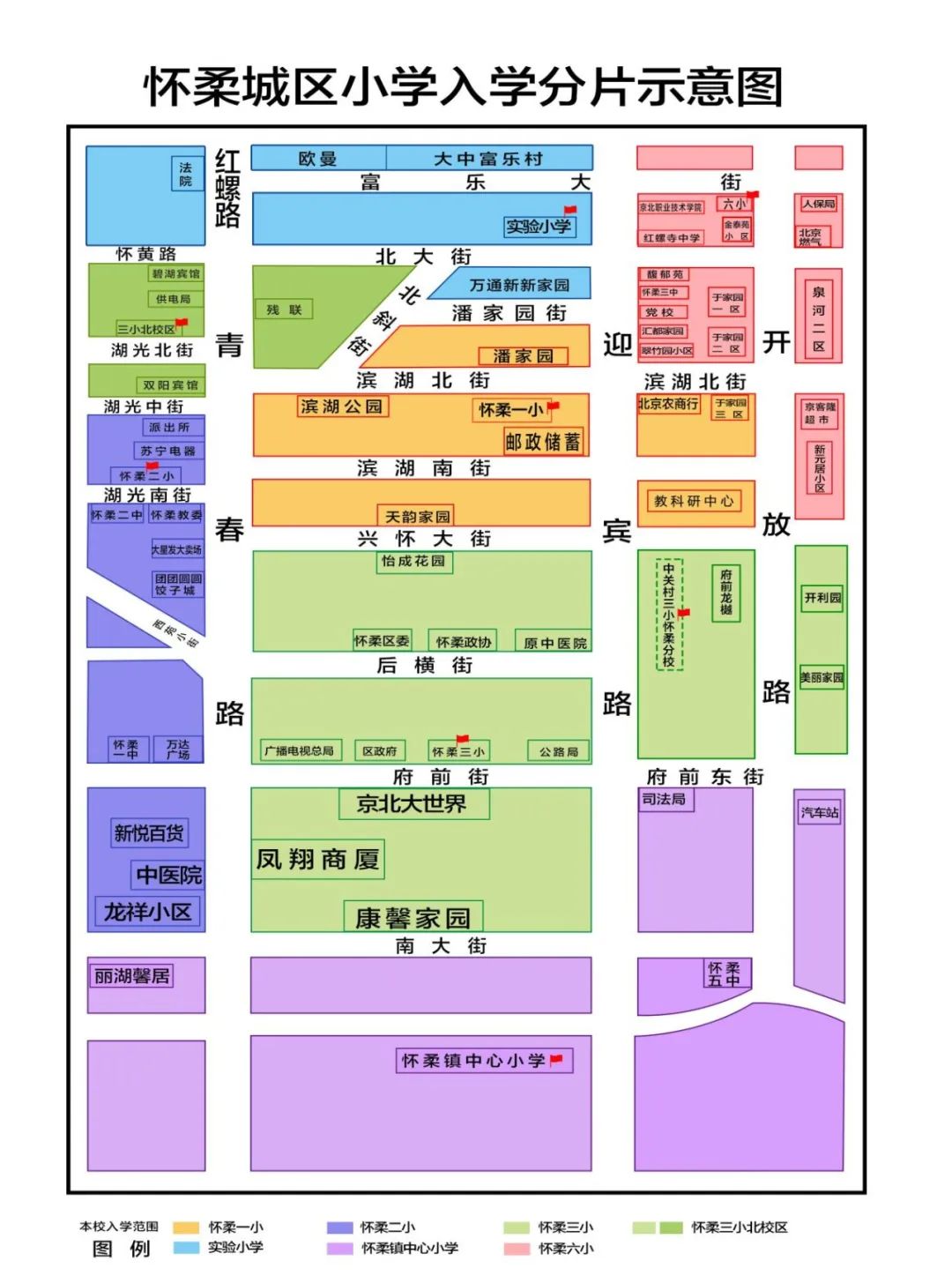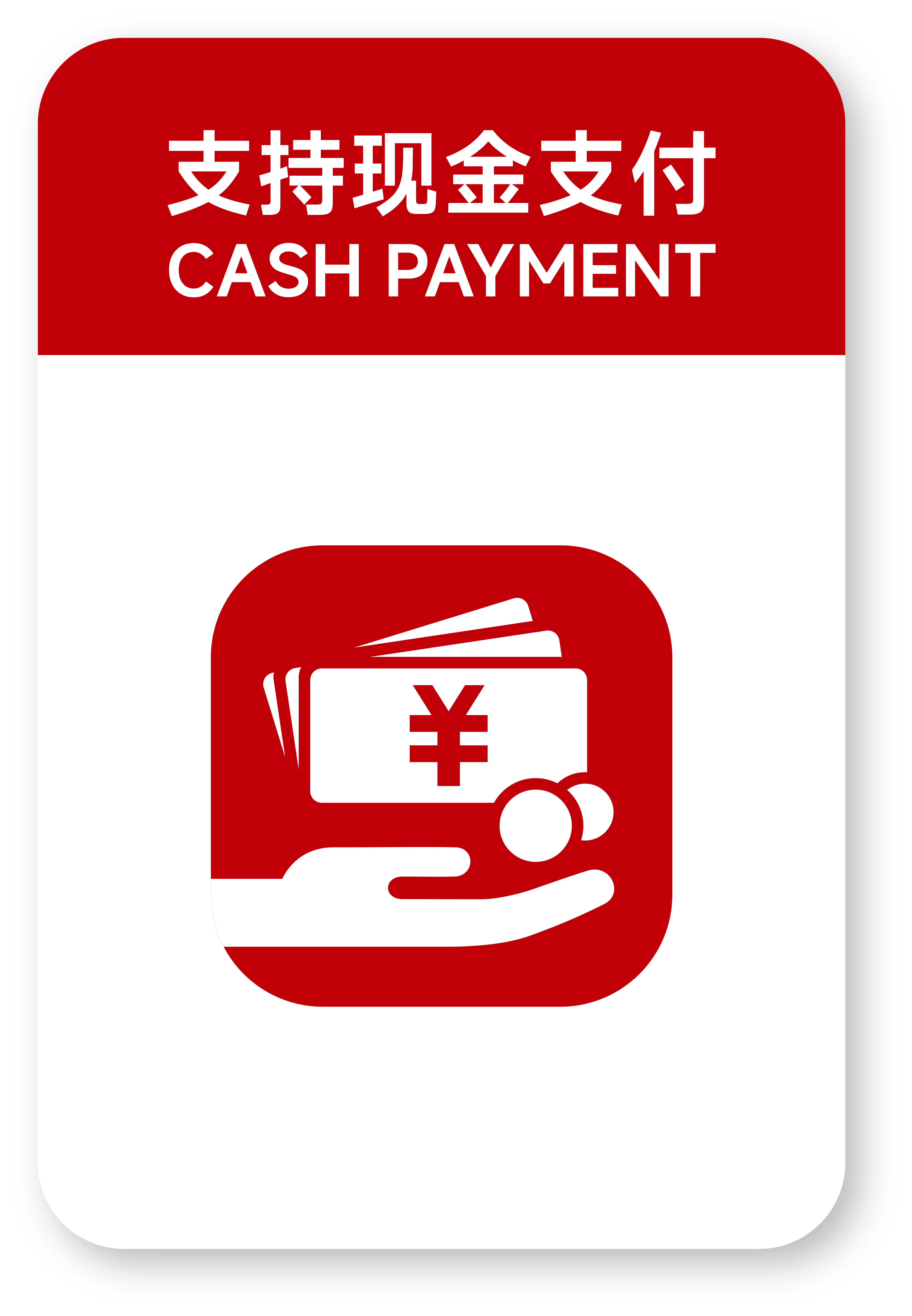那些進過ICU後想到的事
 視覺中國供圖
視覺中國供圖今年過年前,外公進了ICU。在他已經包好了給孫輩重孫輩的紅包、選定了年夜飯的酒店,計劃好了開春後的生活,他腦幹中的血管瘤卻毫無徵兆地破裂了。老人瞬間昏迷,搶救後依靠機器生存,沒有醒來的跡象,直到今天。
等我回到家,家人才告知這一切。我再次見外公,是在ICU每天半小時的探視時間。十幾張床位,每張病床上都躺著一個家庭的悲傷。看著毫無知覺、插滿管子的外公,我很難接受這樣的見面。
第一次直面「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個先來」這句話的殘酷。其實自從離家上大學又留在外地工作,與老人的見面機會就不多了,但終究覺得還有下一次。對生命的認識,在ICU里能得到一次升級,可如果到了這一刻才知道一些事情,終歸還是晚了一些。
翻譯過《沉思錄》的北大哲學系教授何懷宏,早在1996年就出版過一本《珍重生命》,給孩子講生命與死亡。20多年來,書不斷增訂再版,一代一代的孩子出生、長大,面臨著同樣的困惑,有時候是恐懼。比如,即便我們萬分小心、一切順利,在生活中還是不得不面對各種死亡;而如果死亡終將來臨,我們又該如何活著?
我的生命教育最早來自一年一度的清明節,這可能也是大多數中國孩子的經歷。在我的家鄉、南方的一座小城,掃墓稱為「上墳」——確實是要上山的,在植被茂密的山頭,披荊斬棘地找路。與其說是祭奠,從氣氛上這更像是春遊,家族的人難得聚在一起,帶著吃的喝的——後來發展為肯德基麥當勞——讓祖宗也嚐嚐鮮,還要去摘滿山的映山紅……
中國古人是有智慧的,把紀念逝者的清明節放在草長鶯飛的春天,一歲一枯榮的原上草讓踏青掃墓的人也感受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仔細想想,很多時候我們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突如其來、沒有告別的死亡,或者歷經痛苦之後的死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最近出版了一本新書——《生命的最後一公里:關於死亡,我們知道什麼,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該如何面對》,作者是德國安寧療護醫學的領軍者基恩·波拉西奧教授。他曾是神經外科的專科醫生,但在接觸病患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如何保證患者生命終末期的生存質量,成為一般的醫療措施無法解決的難題。
減少過度治療、完成生前預囑等措施,或許可以成為我們這一代人對自己生命更好的把握。越來越多的人——至少我是這麼想的,自己要有機會來決定,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可以或者不可以使用哪些措施。比如,我不願意切開氣管維持永遠不會醒來的生命。
也許,死亡也像愛默生不朽的詩句:如果我的小船沉沒,它是到了另一個海上。
我見過不少人,在退休直至死亡的二三十年,乃至三四十年,這段佔據人生三分之一時長的漫長時間里,每天的日子是如此單一重覆,用「幾十年如一日」來形容並不誇張,生命中那些值得提起的故事也停留在幾十年前。
於是,我鼓勵年輕時沒怎麼出過遠門的媽媽多出去玩玩,對天天健身但依然練不出腹肌的爸爸不吝讚美,我希望自己在老去後依然有跟上時代的勇氣與能力,有獨處的空間,有老朋友可以聊八卦,如果還能黃昏戀也未嚐不可。總之,那時候,我只是老了,但還在好好活著。
有部名叫《不虛此行》的電影,講的是一個編劇以寫悼詞為生,在這個過程中,慰藉他人,也治癒自己。工作原因,十餘年來,我也寫過很多名人訃聞,其中不少在其生前有過直接接觸,最後一次提及卻是去世的消息。
有人生不逢時,在退休後才開始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幸好老天假年;有人去世前還在孜孜不倦寫自傳,可惜這部傳記永遠沒有結尾了;有人跨越3個世紀,見證了什麼是滄桑巨變……
我曾經對外公作過一個簡單的「口述史」記錄。20世紀30年代生人的他,講到小時候是如何讀私塾,羨慕同學的「雞牌」德國鉛筆;十幾歲沒有條件再讀初中,作為長子給家裡開的花布米店幹活兒,背上一根「六尺竿」去鄉間收布;他驕傲地說起自己如何打得一手好算盤,走南闖北,第一次吃到山東的大蔥和饅頭是多麼好吃……這是諸多體驗的一生。
我作為旁觀者,漸漸地也有了一個小目標,健康生活、保持圍觀。到了不得不走的時候,提前告別。多部電影中有「生前葬禮」的橋段,我也和朋友討論過,得出一致結論,死後最想幹的事——如果能的話——就想看看周圍人的反應。
正常情況下,我們是看不到自己的葬禮的,也聽不到大家對自己的評價。所以,倒也不必特地辦「生前葬禮」,但告別確實很重要,與周圍的人告別,也與自己告別。
最後,悄然離去,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4年04月18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