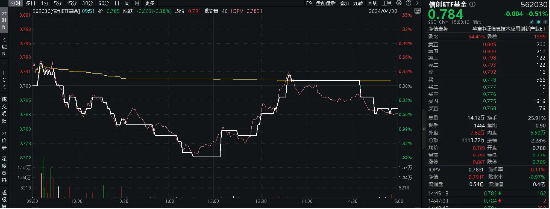《風再起時》:寫給香港電影的一封情書
曾於里
註:本文有劇透
如果抱著“香港梟雄電影”這樣的期待走進影院,很可能會有強烈的落差。從某種層面上看,《風再起時》有點像春節檔的《無名》,都是以相當個性化、藝術化的鏡頭語言去講述類型故事。程耳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美學體系,翁子光更偏向於王家衛的學徒。
在類型上,《風再起時》並沒有掙脫香港梟雄電影的一些敘事特色。
 《風再起時》海報
《風再起時》海報香港梟雄電影緣起於1991年的《跛豪》,其以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橫行一時的毒梟吳錫豪為原型(電影中更名為“吳國豪”),講述了他的傳奇人生。《跛豪》票房口碑雙豐收,擅長跟風的香港電影很快出現了不少以真實的梟雄為原型的電影。比如以“香港四大探長”排名第一、又有“五億探長”(指涉其貪汙後家產高達5億)之稱的呂樂為原型的《五億探長雷洛傳》,以“四大探長”中排名第二的藍剛為原型的《藍江傳之反飛組風雲》。之後的梟雄電影斷斷續續,晚近比較有名的是2017年的《追龍》,甄子丹飾演伍世豪(原型就是吳錫豪),劉德華飾演雷洛(原型就是呂樂)。
 《五億探長雷洛傳》和《追龍》,均由劉德華飾演雷洛
《五億探長雷洛傳》和《追龍》,均由劉德華飾演雷洛梟雄片與黑幫片、警匪片分享著很多相似的戲劇結構,但梟雄片獨具特色的地方在於,它基本上都是以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些真實的梟雄為原型,它不是嚴謹的傳記電影,也不是全然的虛構,更像是基於一定曆史事實基礎上的“捕風捉影”。與其說重點在於“捕風捉影”,毋寧說重點在於“曆史事實”,在於“再現”梟雄崛起經曆背後所承載的共同的香港曆史記憶。
在《跛豪》《五億探長雷洛傳》《追龍》等類型特徵明顯的梟雄電影中,梟雄的崛起傳奇背後分享著共同的香港敘事:1950-1970年代英國政府殖民下的香港,各方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黑惡勢力滲透到香港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吃苦耐勞、勤懇堅韌的香港小人物,還是能夠在亂世中找到發跡的路徑。譬如五億探長呂樂,出身廣東的底層漁民家庭,跟隨家人來到香港避難,兒時在香港吃盡苦頭,之後進入香港警隊,與黑社會關係交好,節節上升,成為“總探長”。
早期的梟雄片,不論創作者還是觀眾對於梟雄的態度都非常曖昧:知道他們不是好人,也會簡略刻畫下他們不好的下場,但影片的重點是對他們發跡史、尤其是發跡後威風八面人生的濃墨重彩,由此寄予著觀眾的發跡想像,進一步鞏固著“小人物以奮鬥改變命運、逆境求生、頑強不息”的香港精神。
梟雄片崛起於1990年代,也沒落於1990年代,梟雄片之後很快出現的是《古惑仔》系列這類淡化香港曆史、聚焦當下黑幫現象的古惑仔片,這個流變背後既有著香港電影的轉摺痕跡,也是香港觀眾迭代的體現:缺乏生活經驗,對曆史相對淡漠的年輕觀眾,更傾向於選擇扁平化的娛樂故事。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風再起時》可謂“反其道而行之”。它不是扁平化、娛樂化的黑幫敘事,作為導演“給香港電影的一個情書”,梟雄崛起背後的“曆史記憶”才是影片的重點。它也不同於《跛豪》《五億探長雷洛傳》,以梟雄的發跡隱喻小人物的奮鬥精神,《風再起時》是以梟雄的傳奇經曆為前景,它的幕布是上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香港斑駁的曆史畫卷。
就比如磊樂(郭富城 飾)發跡前的淒慘經曆,就為觀眾串聯起香港那段屈辱的曆史:港英政府統治前期,華人地位低下;香港淪陷時期,香港人備受摧殘蹂躪,磊樂也是在這個階段永失他一生的至愛小瑜(春夏 飾),同時,“517號”背後是他的死裡逃生,也是他人性的墮落時刻;之後磊樂在香港警隊的步步晉陞,亦串聯起香港1950年代到70年代的諸多時政大事……
 磊樂(郭富城 飾)
磊樂(郭富城 飾)至於磊樂發跡後,《風再起時》的筆墨多少帶有“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意味,對他發跡後在慾望中的沉溺有諸多嘲諷。
相形之下,另外一個總探長南江(梁朝偉 飾),以及磊樂的妻子蔡真(杜鵑 飾),得到導演明顯的偏愛,雖然他們人性中也都存在晦暗陰鬱的部分,但他們理性、克製,始終帶有一種不動聲色的情調。
 南江(梁朝偉 飾)
南江(梁朝偉 飾)情調,是《風再起時》影像風格最大特徵。它不是《追龍》那一類快節奏、強敘事、也不過分講究的影像語言,它是以王家衛的風格講述香港梟雄往事,緩慢、精細、腔調十足。就像南江對蔡真克製又洶湧的情感表達,梁朝偉拿的是《花樣年華》的老劇本,杜鵑要複製的是張曼玉。
 蔡真(杜鵑 飾)
蔡真(杜鵑 飾)旖旎的情調,曲折的曆史脈絡,充滿血淚的成長曆程與迷失慾望的人性掙紮……這一切構成了梟雄片《風再起時》的獨特風貌。撇開電影結尾(廉政公署的出現),以及呂樂、藍剛等人物的真實經曆不談,《風再起時》稱得上是給香港的一封情書,它要表達的大概是香港這座城市的“浮沉感”。就像是香港作家西西那篇超現實主義小說《浮城誌異》所寄寓的,香港是一座“浮城”,因為文化的混雜與身份的迷失,“懸在半空中,既不上升,也不下沉,即使有風掠過,它也不外是略略晃擺晃擺,彷彿正好做一陣子蕩鞦韆的遊戲”,“沒有根而生活”。
矛盾的是,這封情書的另一面,它確實是一部梟雄片,它確實是以呂樂、藍剛為原型,他們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警隊建立了一個貪腐帝國,個人是發跡了,但對於當時普通的香港市民來說,那是一段不賄賂就不能正常生活的晦暗歲月。電影最末,廉政公署長官李子超(許冠文 飾)有著振聾發聵的總結,警察收黑錢不是華人社會里的“禮尚往來”,而是“禮崩樂壞”。
 廉政公署長官李子超(許冠文 飾)
廉政公署長官李子超(許冠文 飾)或許是許冠文駁斥港英政府不作為的那段對話太有力,也或許是許冠文演技太好了,總之看到這裏,觀眾是很容易代入他的視角:對這幫貪腐的梟雄,帶有憎惡。
接著筆鋒一轉,磊樂與南山都跟他們現實中的原型一樣,哪怕有廉政公署的通緝令,他們還是帶著巨額財富成功外逃,在異國他鄉安然終老。
電影的問題不是出在曆史的幕布上,而是台前的表演,或許從一開始就選錯了對象。如果電影不要走梟雄片路線,而是直接採用虛構的人物,也給人物安排一個更具宿命意味的結尾,那麼台前的故事(個人的浮沉)與曆史的幕布(曆史的浮沉),就完美融合為一體,那就真有可能是“香港教父”或“香港往事”。退而求其次,要採用梟雄片視角也可,但結尾不要用那種含情脈脈的鏡頭去刻畫他們的晚年,好像他們真的“無根”似的(人家可是裹挾巨大財富跑的)。
如今電影的處理則變成了:曆史確實在浮沉,梟雄在成為梟雄前也一度浮沉,可成為梟雄後,他們將城市置於禮崩樂壞的境地,最後永遠地逃之夭夭了。他們如何配得上成為這座城市悲情曆史的代言人?
如果寫給一座城市的情書,選擇的是一度與她共成長、但後來糟蹋了她、最終遠離和拋棄了她、卻口口聲聲還愛著她的人作為主角,觀眾不見得能與這樣的主角產生共情。這封情書有可能成為創作者的顧影自憐、自我感動,哪怕情書有外力刪改的痕跡,它台前故事的立場終究是尷尬的。
本期高級編輯 周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