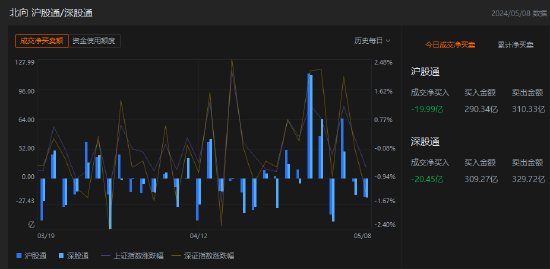新書|蔡駿《謊言之子》:16年謎案背後的悲劇和秘密
“我們為什麼說謊?”
對於從事懸疑寫作二十年的蔡駿來說,“謊言”有時是不得已的選擇。在新作《謊言之子》中,他講述了一個構建在謊言之上的故事,以此折射出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掙紮與無奈。3月12日,蔡駿與作家那多、走走做客上海鍾書閣,與讀者剖析《謊言之子》中兩樁跨越16年的謎案,以及案件背後的悲劇和秘密。
 《謊言之子》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新近出版
《謊言之子》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新近出版原生家庭有時是疊加在孩子身上的惡
16年前的清明夜,上海郊區工地上發現一具面目全非且被剪斷手指的屍體。刑警許大慶查案未果,不久妻子文雅向他提出離婚,隨後在家中自殺。16年後,許大慶在妻子遺物中發現她與一個陌生男人的親密合影。當一起連環車禍打開了塵封多年的“潘多拉之盒”,一場盤根錯節的死亡迷局被再次引爆。
而對於這場迷局,小說的名字或許給出了些許答案。蔡駿透露,《謊言之子》的最初構想是以一個孩子的“犯罪”為核心。“作為作家,我更關注當下與未來。而孩子是中國的當下以及中國的未來。”在創作過程中,蔡駿不斷加入一家三口等元素,為孩子的“犯罪”裹上一層懸疑的外衣,把個體的“謊言”變成了一群人的“謊言”。“這代表了我對社會的一些看法,比如原生家庭的影響有時是疊加在孩子身上的惡。沒有犯罪的人並不意味著不是一個惡人。很多時候,有些人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內‘犯罪’。”
為了營造一種羅生門式的藝術效果,小說敘述分為陰面和陽面。蔡駿說,文學作品中有兩種謊言,一種是人物意義上的謊言,通過人物各種各樣的目的來營造出迷惑性的假象,另一種則是作家意義上的謊言,這是文學技巧的一部分。兩種謊言融合在一起,會構成獨特的魅力。
“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交織著個體與集體的‘謊言’,維持著社會的假象。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才衍生出了很多懸疑犯罪小說中所涉及到的那些光怪陸離的故事。”蔡駿說。
 蔡駿
蔡駿看到的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遊戲
走走認為,蔡駿的創作更側重於探討真實的社會議題,表現出更深的社會關照。《謊言之子》基於家庭的情感走向已經有了日本社會派推理的傾向,體現了東方式的創作理念。中西方的推理懸疑雖然都源於因果論,但東方的因果論中有更多的情感羈絆,歐美則更注重展現犯罪的科技走向,有一套完整的犯罪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
那多也觀察到《謊言之子》對於真實案件的影射和延伸。在《謊言之子》中,人們如何戴上面具,並為此付出了怎樣的代價?這樣的主題很能讓讀者產生共鳴。本格、新本格可能更注重謎團、密室,更具遊戲性和娛樂性,但社會派更注重情感,這種共情感是讀者喜歡這一類型小說的原因。
那多表示:“在社會派推理中你會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小說中的故事是有可能發生的,我們能看到一個人‘從哪裡來,如何走到殺人的那一步,之後又往哪裡去’。我們會感到在生活中做錯一個選擇也有可能變成和小說中人物一樣的處境。這是讀者喜歡這類小說的原因,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遊戲。”
 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回歸創作的原點,找到筆下的“現實”
拓展到整個文學的維度,走走分析了包括懸疑推理小說在內的類型文學與純文學的區別。純文學傾向於從宏觀角度上去看待細節對人的影響,就像“蝴蝶效應”,樂於構想一個罪案如何改變一個人的一生。而類型文學更關注人的犯罪動機。《謊言之子》中“人的身份被篡改”的細節讓走走看到了當下中國推理開始有了把社會和真相放進來的努力。
她認為最好的懸疑小說不是敘述詭計的那一類,不局限於刑偵、法醫學的範疇,還需要心理學、社會學,甚至廣告學等等學科的內容。同時,一部沒有遺憾的懸疑作品還要能系統地處理時代背景下的社會價值觀、意識形態以及尖銳的現實矛盾。
“生活永遠比小說更曲折離奇。”那多表示,真實案件中往往存在很多普通人難以想像的、非理性非邏輯的因素,這些反而需要在小說創作中得到梳理,需要小說家通過由虛化實的方式讓讀者信服。這意味著,小說家在走進真實案件的同時,又要能做到從真實案件中走出來,回歸創作的原點,找到筆下的“現實”。